85年前,上海文化界如何宣传阐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2025-01-09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顿文聪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即后来定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对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海文化界迅速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宣传、研究与阐释,上海由此成为当时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当时,上海虽处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孤岛”后期,但上海文化界仍然突破重重困难,在报纸、杂志、出版机构发表数十种文章及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文学等多角度多层面宣传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自觉运用新民主主义从事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宣传和阐释特色鲜明、量质俱佳,颇能代表当时党内外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新民主主义宣传阐释史上的光辉一页。

1940年1月4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月9日下午,毛泽东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月20日《新中华报》特写稿摘录该演讲稿核心内容1000余字
上海“孤岛”时期指的是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至1941年12月日军侵入租界这一时期,1940年至1941年是为“孤岛”后期。“孤岛”后期,上海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新闻出版环境变差,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新闻出版事业规模大为收缩,许多报刊杂志刚出版就被封禁。在此背景下,一些当时在上海从事文艺文化工作的老同志认为,“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特别是文学凋零、成果惨淡、乏善可陈;但党史著作一般认为,在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孤岛”文化较为繁荣、成绩卓著,如创办多种报刊杂志、组建多家出版机构出版革命书籍、拓展戏剧电影队伍。客观地看,“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实际上仍较有作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后,上海文化界不仅突破重重困难出版多版本《新民主主义论》,并及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学习、研究、阐释和应用。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产生了85种文章及著作,是为当时宣传和阐释新民主主义理论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深刻影响了上海、香港等地区以及苏北、苏中、江南抗日根据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文化理论的把握与阐释非常精准,如上海文化界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新类型的文化,区别于旧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新形态;将“民主的”文化纲领解释为“大众的民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维度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欧美式的虚伪的民主,其对象不再是抽象的“全民”“国民”以及代表资产阶级的“民族”本位,而是人民为本位,也即以工农大众为核心的、联合其他革命阶级的政权联盟的民主,因此也是“大众的民主”,这一理解与毛泽东的文化民主观基本一致,早于1942年前后《新民主主义论》修改时加入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论断。
目前学界研究“孤岛”文学的学者对“孤岛”时期的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虽涉及本文要述及的王任叔、李平心等人,但关于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的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揭示、宣传和应用的研究很少。研究《新民主主义论》在上海或知识界传播、阅读、阐释的文章虽有关注到李平心等人的相关论述,但将“孤岛”时期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宣传阐释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还未看到。因此,笔者爬梳在中共江苏省委各运动委员会等领导下,报刊杂志及进步出版机构刊登或发行的关于宣传、阐释与应用新民主主义的论著,从整体上把握和讨论“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论》的学习、宣传、阐释及其特点,以期进一步深化《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史、阅读史、宣传阐释史研究。
01.《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上海地方党组织采取紧紧依靠文化界,多办报纸刊物、多宣传的策略,“以文化战线为突破口,作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之枢纽,利用刊物扩大影响,发动群众,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实践证明,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八办”(上海八路军办事处)以及上海文协在党领导下的进步书刊、出版机构大力宣传新民主主义,收到了良好的宣传统战效果。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经反复修改后于2月20日在《解放》周刊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原计划2月1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延宕至3月下旬以原演讲题目发表。中共中央利用电报广播、党报党刊、组织传达等多种形式对《新民主主义论》进行了宣传。《新民主主义论》至少在3月时已经传入上海地区,单行本全文应在5月底至6月传入。

文代会后,毛泽东对演讲稿反复修改并广泛征求意见。1940年2月20日,《解放》刊发《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2月1日,延安广播台开播,向各根据地广播党内文件或指示。2月初,延安广播台广播了《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发表的《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写中刊载的毛泽东演讲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及第一次文代会宣言。上海“八办”也通过广播电台渠道收到,并在“八办”主办的《内地通讯》上刊发。3月25日,上海大众呼声社(江苏省委职委所属)出版《大众呼声集:在饥饿线上》,特载毛泽东《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一文件着重强调“日寇配合政治进攻对我进步文化极尽摧残破坏之能事,进步文化人文化启蒙运动加强民族战斗的勇气与实力,促进宪政反对复古倒退运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在早期传播中有一技术原因导致的“失误”,影响了各地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早期接受与认识。
1940年4月10日,《群众》刊载《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经常被学者引用为《新民主主义论》在重庆传播的重要证据,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该文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该文是《群众》转录的《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2月11日第4版内容,编者按也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所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者按指出,这篇文章是延安发给各根据地的电文,由于技术条件缺失了千余字,因此,认为这篇文章为毛泽东1月9日的演讲。这篇文章实由两篇文章组成:一是《新中华报》特写中刊载的《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篇文章除第一句话被转录以外,下文均缺失;二是文代会宣言,从缺文开始至文尾为文代会宣言第二段以至文末内容。由于《新华日报》(华北版)接收电报之开头为“毛泽东同志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中间又缺失文代会宣言题目及其第一段,因而认为电报传来的文章均为毛泽东的演讲,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以致出现重要误判。更为关键的是,这客观上导致延安之外接收到的实际上是文代会宣言,而这一宣言当时使用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概念,及大会宣传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这是导致后来党内外人士特别是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认识出现偏差的一大重要原因。

1940年2月1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转发《新中华报》刊发的毛泽东演讲摘要《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因技术问题,摘要稿仅接收到第一句话,其余文字缺失;剩余部分为文代会宣言内容。因此,该文被误认为毛泽东演讲稿。该文为《群众》1940年4月10日全文转载,又被认为是重庆地区公开宣传《新民主主义论》之肇始,实为文代会宣言
1940年4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职员运动委员会机关报《职业生活》出版“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特辑,刊发王开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无咎《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何逸清《建设上海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3篇文章。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文协领导党内和进步人士以《上海周报》《学习》《新知》《哲学》《四十年代》《求知文丛》等报刊杂志,北社、十年书店、一般书店、新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为阵地刊登和发行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的作品。如5月4日,无咎在《上海周报》发表《再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5月11日,李平心在《上海周报》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溯源与新启蒙运动的重估》,其篇前题记称:“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后来又看到友人送给我的一个印刷比较齐全的文献的一片段——《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作者,即上述演讲者著的)第四段至第十段。”这里李平心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论》第四至第十段,指的是1940年3月10日延安新华社向各地广播的《新民主主义论》之第四至第十段。该片段仅包含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及驳斥各种理论,并不包含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内容。6月1日,上海《学习》刊登十年出版社《新民主主义论》书目广告:“介绍当代革命导师的《新民主主义论》十年出版社定价二角·各大书店均有出售”,但并非全文。可见,5月时,《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尚未传入上海地区;上海地区接受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概念及文代会宣言中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及“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

1940年4月24日,中共江苏省委职委所属《职业生活》杂志,刊登三篇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文章
不过,6月29日、7月1日,《上海周报》《学习》已刊登香港光大出版社发行的《新民主主义论》(全文)的书目广告:“当代革命导师的权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已经出版了。这是一本伟大的历史文献,它把过去中国二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给一个确切的结论;今后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动向,给以一个明确的指示。刻绘出新中国光明壮丽的远景。无疑义的,将是一本人人必读人人必备的好书。”可见《新民主主义论》全文或解放社3月单行本、《解放》周刊、《中国文化》等书刊大致是在6月前后传入上海。

1940年6月29日,《上海周报》刊登香港光大出版社版《新民主主义论》推介,该版本为全文足本
到了1940年冬,上海已经出版了3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十年出版社本为节本,其余两个版本为全文,即1941年1月1日出版的《学习》之《一年来新书目》编入的光大出版《新民主主义论》(全文),2月16日《学习》之《一年来新书目·续目》又编入无出版社信息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可见,《新民主主义论》在国民党1940年6月13日通电全国查禁之后仍然以原著者、原书名在上海地区出版、经销多种版本,当然这与上海租界有着重要关系。
02.上海文化界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
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八办”收到《新民主主义论》部分文稿及全文后,除进行组织内传达学习,还通过各直属运动委员会的阵地进行大力宣传,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有力推动了新民主主义在“孤岛”的传播和宣传。笔者搜索了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八办”领导下各运动委员会、文协、学协等主办的报刊、杂志及出版社,如“八办”主办的《内地通讯》、职委所属的《大众呼声集》《职业生活》、文委领导的《上海周报》《学习》《求知文丛》《奔流文艺丛刊》、学委领导下的上海学协的《青年知识》、工委成立的秘密出版机构——北社,查得85种相关文献(除文代会宣言的来件、《新民主主义论》各版本)。
从整体来看,85种文献主要由35人完成。王任叔(笔名:无咎、无邪、巴人、庄师宗、铁夫、胡自)16篇(册)、李平心(笔名:万流、青之)7篇(册)、陆象贤(笔名:列车、列御寇)6篇(册)、黄特(笔名:生力)5篇(册)、翼云5篇、姚溱(笔名:阿隼)4篇、陈次园(笔名:陈垦、宋无、方兴)3篇(册)、郭风(笔名:苏明)3篇(册)、陈公琪(笔名:丁宗恩、北辰)3篇(册)、蒋天佐(笔名:史笃)2篇、赵平生(笔名:则鸣、方舟)2篇、朱善钧(笔名:方耀)2篇(册)、俊鸣2篇,这13人共计完成了60篇(册),占全部文献比重超70%。其中,艾寒松(笔名:阿平)、王任叔当时为江苏省委文委委员;胡愈之、陈公琪、蒋天佐、蒋锡金(笔名:霍亨)、姚溱为中共党员;李平心早年便为中共党员,后主要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进步运动;陆象贤为秘密出版机构北社社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次园、周木斋、俞鸿犹(笔名:弘远)、包文棣(笔名:闻歌,1942年入党)、马健为当时著名的文化界进步人士,其他如翼云、俊鸣等笔名暂未查找到真名,还有如博古(笔名:则民)等知名党员发表了宣传阐释文章。《职业生活》《文艺新潮》《上海周报》《学习》《哲学》《求知文丛》等报刊杂志均为江苏省委及其领导下的上海文协所主办的刊物;北社、珠林书店、国泰出版社、一般书店、十年书店、新人出版社、香港书店等为中共江苏省委或进步人士主办的公开、半公开甚至秘密出版社。有的出版机构为化名,如北社即为秘密出版机构,其印刷、发行均靠开明书店工作的张纯嘉支持、代办,负责北社的陆象贤并未向其透漏这是上海党组织主办的出版机构。北社的出版物采取半公开方式发行,一部分通过报摊销售,一部分由邮局中的中共党组织邮运至华中、淮南抗日根据地或运送至大后方,一部分通过上海、香港等地的经售商代售。
按照以上文献史料及《新民主主义论》在上海地区的传播情况,可将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及其文化论的宣传阐释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40年4月至6月,为上海文化界学习、宣传以及初步阐释新民主主义的时期,侧重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哲学及新民主主义整体上的介绍和把握。这一时期共产生了16篇宣传阐释文章和2本著作,如《职业生活》率先刊发“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合辑,王开道的文章主要介绍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及其内容,王任叔、何逸清的文章已开始阐释和运用新民主主义;《上海周报》陆续发表艾寒松、王任叔、李平心、胡愈之等人7篇文章,主要为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与革命运动相结合、驳斥国民党御用文人发起的“民族文化”论争、阐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与任务;《文艺新潮》发表了蒋天佐、蒋锡金的文章,主张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展和研究文艺运动;《新知》《学习》《青年知识》等刊物则简要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又如王任叔的《文学读本》于5月出版、11月又出版了5月已经写毕的《文学读本续编》,书中已经自觉使用新民主主义理论来探讨文学运动和文学理论。特别是其5月出版的《文学读本》,其实当时他已完成该书写作,但仍在该书出版之际在多处加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如认为完成了反日反汉奸的抗战文艺,将必然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的新民主主义文艺;鲁迅先生的创作全部差不多可以说是他反封建反帝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白;我们的社会正是向反封建反帝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前进;等等。

1940年5月,王任叔曾在上海珠林书店出版《文学读本》;11月又出版其5月份写毕的《文学读本续编》。两书均自觉使用新民主主义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对当时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这一阶段,由于《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尚未传入上海,上海文化界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时使用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梗概稿、文代会宣言及《新民主主义论》第四至第十段内容,这就导致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和运用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因当时看到的是文代会宣言中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表述,使得他们均以此为准进行阐释和宣介。
(二)第二阶段。1940年8月至1941年12月,是深入研究、宣传、阐释和应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期。这一阶段共产生了52篇宣传阐释文章和15本著作,将新民主主义理论运用到各方面。以新民主主义进行文化、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等理论研究,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新风向。
以著作为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刘宁一找到当时在上海邮政局工作的陈公琪商议,在工人中宣传《新民主主义论》,由陈公琪、陆象贤、朱善钧三人合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后以《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前途》重版)。《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分为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与国际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3章,以较为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中国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异同、新民主主义的原则政策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该书写成之后,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秘密出版机构——北社来出版。1940年9月,《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出版,首印5000册旋即销售一空,二印5000册也很快售罄,反映了上海各界对通俗理论读物的需求。

1940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秘密出版机构——北社出版《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首印5000册旋即销售一空,再印5000册也很快售罄,反映了上海各界对通俗理论读物的需求
新民主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其他著作还有不少。如1940年10月王任叔的《论鲁迅的杂文》出版、11月他的《文学读本续编》出版、1941年11月列车(陆象贤)的《两极集》出版。特别是北社社长陆象贤的《两极集》(部分文章后收入《爝火集》)为当时研究新民主主义诗歌理论的佳作。他主张将原来那种观念的、被动的、观赏的叙事诗、浪漫主义诗歌,也即少数士大夫的小玩意、小摆设的诗歌,转向自发的、能动的、深入的抒情诗、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以深入大众、反映人民群众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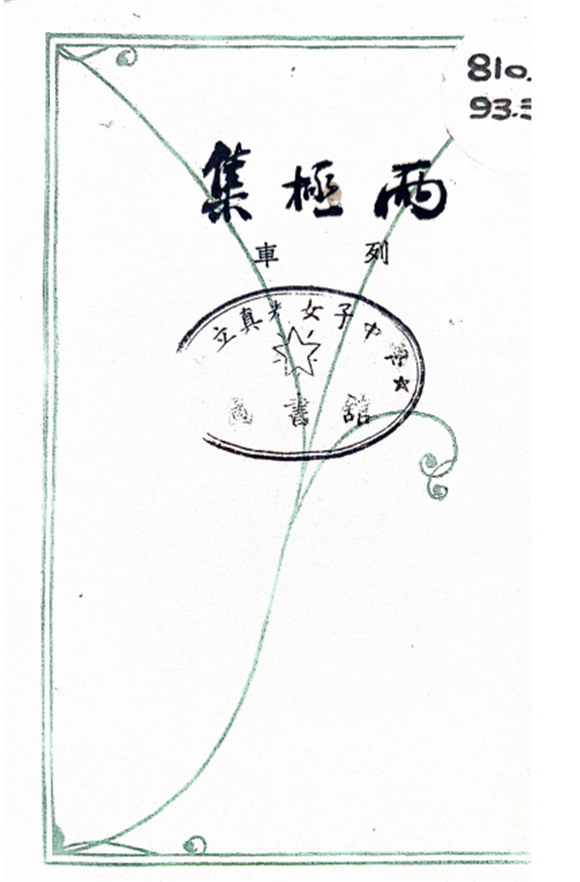
1941年11月,陆象贤(列车)在北社出版《两极集》,对当时的新民主主义诗歌运动、新民主主义新诗理论多有论述
李平心、周木斋、马健等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1940年8月李平心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出版、1941年1月周木斋的《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出版、马健的《论国共合作》1941年出版(1946年再版时更名为《国共合作史》)均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政治的佳作。陈次园(宋无)等人的新民主主义哲学研究亦可圈可点。1941年3月出版的宋无的《新民主主义哲学论》以3万字的篇幅介绍了新民主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特征及当前工作者的任务,被时人认为很好地融合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与张闻天《新文化运动论》。

1941年3月,宋无(陈次园)出版《新民主主义哲学论》,阐发新民主主义哲学的特征及新民主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面,有陆象贤《新中国经济地理教程》、阿隼(姚溱)《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等著述。时年20岁的姚溱发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文,在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发挥,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内容兼具“资本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主要在于消除和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顺利条件,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一定的物质前提。为了推翻这种障碍,必须进行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改革,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关系。他提出的各项举措基本上被《论联合政府》吸收,堪称前瞻性研究的典范。
03.上海文化界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的特点
“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的宣传和阐释量质俱佳,颇能代表当时党内外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政论文和论战文章的形式宣传阐释新民主主义。上海“孤岛”后期由于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对租界的施压,租界内形势变得相当严峻,除日伪大肆宣扬“新民主义”“王道协和”“东亚共荣”等奴隶文化之外,当时一帮国民党御用文人还发起了“民族文化”“民族哲学”“民族文学”运动,企图建立起以“民族”“全民”为标榜的资产阶级民族文化运动,本质是构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文化体系。因此,上海文化界除用小说、散文、戏剧、歌曲、漫画等文学艺术形式回击上述文化逆流外,还运用杂文和政论文的形式发起论战,反击文化逆流。这种形式不同于鲁迅式杂文的松散、辛辣、短小精悍,而以论题集中、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言语激烈、篇幅较长为特征。如王任叔论民族文化的4篇论文:《论民族哲学》(上下)《略论“新民族哲学”》《关于民族文化问题》《叶青简论》;又如子纯《过去中国一年来的思想斗争》、李平心《论现在的中国文化》、李卫文《论文化的逆流》、王任叔《论新专制主义的文化》,均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立场坚决批判了日伪的奴化文化以及如萧一山、冯友兰、张君劢、陈立夫、叶青等的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对上海的文化界人士、普通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结合五四运动纪念日、鲁迅纪念日、新启蒙运动、中国化运动等进行比较研究和宣传。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点,鲁迅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方向,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文化。在前述第一阶段,上海文化界看到的仅为《新民主主义论》演讲梗概及第四至第十段,其读到的文化分期是毛泽东的“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三阶段分期,因此这一时期上海文化界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也将新文化运动分为三阶段,即五四运动至大革命结束、土地革命时期、“一二·九”运动或抗战以来。第二阶段,上海文化界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全文后,已较少论及新文化运动的分期问题。转而因鲁迅逝世四周年,加上陕甘宁边区文代会及毛泽东对“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方向”的高度革命评价,使上海文化界自觉将宣传新民主主义与纪念鲁迅联系起来。新民主主义文化被上海文化界称为一场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运动,一些著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解放意义溯源到1936年至1937年京津沪地区张申府、艾思奇、何干之、柳湜、胡绳等积极参与的新启蒙运动。有的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相联系,认为其是“中国化”“学术中国化”的延伸,“中国化”“学术中国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现实表现。

1941年7月5日,王任叔(无邪)在《上海周报》发表《鲁迅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文化》
(三)对“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的阐释丰富而深刻。上海在收到《新民主主义论》全文之前,因为传播原因,只接收了文代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第四至第十段。文代会宣言带有“新民主主义”“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等概念,张闻天修改发表的演讲报告再次强化了文代会宣言中上述概念。另外,《新民主主义论》早期传播中的第四至第十段并不包含直接涉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别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表述,导致上海文化界仅能就“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等“四纲领”进行阐释宣介。
第一阶段,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解释由于并没有直接、完整的来自于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张闻天的详细阐释,因而带有许多发挥但不乏真知灼见的成分。如王任叔在多篇文章中对“四纲领”的阐释非常具有特色,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他从“中国化”与“民族化”的角度探讨“民族化”,提出了国际文化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主的”,这种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少数人的民主,也不仅是工农阶级的民主,而是一切革命的抗日的革命阶级的民主专政,是“大众的民主”。文学上的民主不是每篇都要写民主问题或涉及民主问题,而是指文学的任务是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即坚持统一战线、争取思想自由、歌颂光明、暴露黑暗等。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其一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科学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科学的历史观也就是先成为新民主主义者而后以新民主主义的眼光、用新民主主义的笔来描写现实。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必须以大众的利益为中心,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在大众文化建立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所谓大众文化不仅是工农大众的教育手段,而且是工农大众之阶级意识——思想情感之传达与表现的一种文化,就文学家的任务而言,文学是为大众的,进而由大众创造。
第二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全文传入之后,上海文化界开始接受和使用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表述,但其阐释仍然使用“四纲领”。特别是9月张闻天演讲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今后的任务》以《新文化运动论》为题在香港光大出版社出版、上海发行之后,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念和阐释,使用张闻天关于“四纲领”的详细解释,一文之中同时引用毛泽东、张闻天两文成为一时之风气。如宋无认为新民主主义哲学具有“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特征,它具有民族的形式和国际革命文化的内容,也即以辩证唯物论作为其中心的内容,以我中华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作为表现其内容的形式;它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的精神武器,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理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领导的文化,是以科学的态度、尊重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之发展的;它代表大众利益的、为大众而斗争的、为大众所有的哲学。因此,四个特征不能机械地划开了理解,不能个别地把握。
04.结语
《新民主主义论》传入上海之后,上海文化界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各方面均展开全面宣传和深入研究,既有整体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研究,也有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文学、哲学等研究;既有千字短文,也有多达二三十万字的专著;既有社论、政论文这种严肃文字,也有随笔、短札这种小巧灵动的文学形式;甚至还编写了“新民主主义(Neo-Democracy)”词条,应是目前最早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词条。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的宣传阐释,对上海、香港等地区以及苏北、苏中、江南抗日根据地均产生了广泛影响,为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及时、快速、准确理解新民主主义提供了重要参考。虽然日伪和国民党大肆破坏上海文化机关、迫害文化界人士,上海文化界宣传阐释的发表阵地《职业生活》《文艺新潮》《上海周报》《学习》《哲学》《四十年代》《求知文丛》等被迫陆续停办,光大版《新民主主义论》《新文化运动论》、东方出版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学读本》《文学读本续编》《中国现代史初编》等遭国民党审查机构扣压查禁,但黑暗毕竟遮不住光芒,“孤岛”后期上海文化界对新民主主义的宣传阐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占据着光辉一页,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