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疆琐忆
2017-03-30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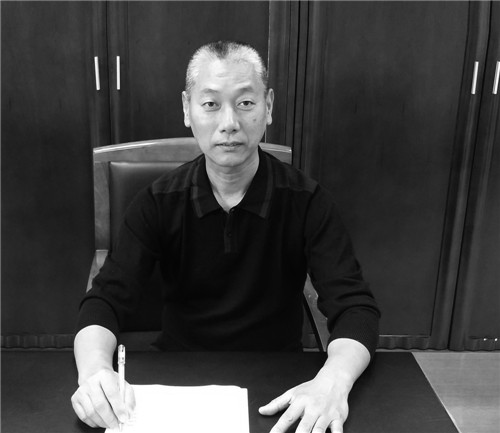
【口述】施耀忠,1957年9月生。现任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财务管理处处长。1997年2月至2000年1月,担任新疆阿克苏地区财政局副局长,上海市第一批援疆干部。
口述:施耀忠
采访:任俊锰
上世纪末的1997年,我有幸成为上海第一批援疆干部的一员,进行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自2000年初回沪至今,已经过去了16个年头。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情都已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淡忘,但三年援疆生活的一些珍贵片断,却至今仍珍藏在我的脑海里。
这些片段对我来说就像一幅画卷,尽管不是出自什么名家之手,但于我却弥足珍贵,毕竟这是我们援疆干部和当地同志们共同用真情绘就的“援疆画卷”。
初尝援疆“苦”
1997年2月20日,我随援疆队伍抵达阿克苏。根据组织的安排,我开始担任阿克苏地区行署财政处党组成员、副处长,并在当年7月进行的地区行署机构改革后,改任地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按照财政局党组的分工,我负责分管文行科、社保科、地区财经学校和地区房管所,并协助局长马木提·阿西尔同志管理预算科。看起来,这几个部门除地区财经学校和地区房管所外,都是权利很大的部门,但实际上也是矛盾最突出的部门,特别是预算科。
说来也巧,该科科长卢维民同志正好是上海宝山人。据了解,他在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阿克苏地区,经过多年的工作锻炼,对财政业务十分精通,与各方面的关系也处理得相当融洽,可以说是地区财政局的中流砥柱。
其实,他当时已经担任副处级的局工会主席,但因工作需要仍兼任预算科科长之职。他曾推心置腹地对我说过,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财政部门特别是财政预算部门,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基本保证全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时拿到每月的工资,已经算是最好的尽职。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不仅描绘了一个当地财政官员面临的窘境,而且成了他们力争完成的切实工作目标。
对此,我也是感同身受。因为到任后,我曾多次陪同马木提局长或者自己带队到阿克苏所有县市进行过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才生切地感受到阿克苏地区面临的巨大财政困难,虽然该地区管辖面积比上海大很多,但经济发展状况相当落后,地区财政严重收不抵支,日常运行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补助。这样的状况,也就造成了地方财政的诸多无奈。

施耀忠(左一)和地区财政局领导一起到阿克苏市托峰棉纺织有限公司考察调研
比如,阿克苏地区下辖的八县一市中,财政状况最差的柯坪县,1996年财政收入几乎为零。有一次,我和马木提局长去调研时,县政府安排我们住在县里的招待所,而房间里的卫生间竟然没有水,招待所的同志费了好大劲才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桶水,让我们洗洗脸、擦擦身。后来才知道,柯坪县面临的最大发展瓶颈也正是水资源匮乏。
当时,这样的情况极大地触动了我。我想,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援疆时间是短暂的,吃些苦也应该,但县里的领导和各部门的同志却每天都在克服诸多困难,在这么艰苦的地方深耕多年,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和斗志,确实令人敬佩。相比之下,在我看来路途遥远且路况很差的外出调研,则根本不值一提。
在与县领导和当地群众沟通后,得知当时的县委书记正带领着领导班子人员和群众在塔里木盆地区域内开荒造地,准备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再造一个柯坪县”。得知此事之后,我和马木提局长都甚为感动,决定亲眼看看这个“新柯坪县”。看到之后才知道,正在建设中的新柯坪,当时已经规模初显,望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群众挥汗如雨、干劲十足,现场指挥人员有条不紊地指导现场工作,想到其美好的远景,我们也感到十分欣慰。
融入新生活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援疆初期,我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就餐问题。
当时地区财政局并没有开设自己的员工食堂,经组织安排,我曾陪同首批上海援疆干部领队、时任阿克苏地委副书记的沈秋余同志一起在地委机关食堂就餐,但由于他与其他地委领导往往会利用就餐时间商量工作,我坐在旁边显然不大合适,这也是我面临的一大窘境。所以,一个多月后我就主动提出回单位自己解决吃饭问题。
阿克苏市城区面积不大,离地区财政局不远处就有菜市场,此外,还有一些郊外的农民兄弟经常提着或挑着自种的时令蔬菜,在大院附近叫卖,买菜显然不成问题。虽然自己的厨艺还达不到一个合格厨师的水平,但一些简单的饭菜自己还是可以做的,最起码不会让自己饿着肚子。
随着和当地同志的接触机会增多,我的口味也有了不小的改变,特别是对大蒜的偏好,就是在援疆的三年里培养起来的。在上海,我家做菜时基本上不放大蒜,可在阿克苏就不一样了,无论是在饭店里吃饭,还是去朋友家吃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每个菜几乎都会放大蒜。
刚开始我还不理解,直到有一次我随马木提局长去乌鲁木齐出差,才有了切身的体会。出发时,由于刚到阿克苏不久,有些水土不服,我还在闹肚子。中午时分,我们寻了家道旁的维吾尔族兄弟开的小饭馆吃饭,看到马木提局长和驾驶员都在剥生大蒜吃,我就问了下原因,才明白新疆好多地方的水质不是很好,而吃生大蒜可以有效杀灭细菌,防止闹肚子。听完这样的解释之后,我尝试着吃了几瓣,感觉还真有效,余下的路途中我的肚子也就慢慢地不闹了。
在以后的援疆岁月里,我也养成了正餐前先吃几瓣生大蒜的习惯,就算回到了上海,我也喜欢在做菜时放些大蒜。
除了就餐问题之外,我和一起援疆的同志还面临着严重的身体健康问题。之前,在上海时,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但到阿克苏后不久,由于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巨大改变,很快得了较为严重的痔疮,胃也出了毛病。
类似情况不止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们组内反应最严重的是颜立强同志(时任地区棉纺厂副厂长),有段时间甚至身体虚弱到不能正常参加工作,经组织批准回上海治疗了一个阶段,才又返回阿克苏。在地区棉纺厂主要领导和其他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下,他很快进入角色,为地区棉纺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友谊重千钧
还记得,我们那批援疆干部一行23人,于1997年2月17日离开上海。而当时新疆刚发生了严重的伊犁地区“2·5”打砸抢暴力事件,维稳形势较为严峻。到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后,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给予了高规格接待,也采取了较为周密的保卫措施,入驻宾馆后,规定一律不得外出,也不允许外面的亲朋好友来探望。
抵疆后的当天晚上,当我刚用完晚餐准备回房间休息时,突然接到了宾馆总台打来的电话,说是自治区政协的领导要来看望我和其他两位上海财政系统来援疆的同志,一位是宝山区财政局副局长华建国同志,另一位是闵行区财政局副局长刘杰同志。
见了面才知道,来看望我们的是自治区政协常委兼自治区财政厅厅长龚金牛同志,随同他来的还有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谢瑄同志。交谈之后,才知道龚金牛厅长也是一个老上海人,支边到新疆后,已经在财政部门工作了好多年,他对我们的到来非常关切,嘘寒问暖,使我们感动不已,亲切感油然而生。
虽然我们到任后不久,龚金牛厅长就光荣退休了。但在以后的三年援疆生活中,他的继任者和自治区财政厅各部门的同志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使我们充分体会到了“天下财政是一家”的温暖。
除了得到来自自治区财政厅同志如朋友般的关怀和帮助外,我在阿克苏地区也结交了很多纯朴、实干的朋友。
阿克苏市区除驻有阿克苏地委、行政公署等党政军机关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师部也驻扎于此。据了解,20世纪60年代,不少的上海知青响应祖国的号召,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来到这里,为支援边疆、建设边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里建功立业,逐渐成长为农一师和地区政府的各级领导和专业人才。

首个援疆项目——阿克苏地区干部培训中心
因此,在阿克苏地区财政局工作的三年中,我和不少当地的同志因工作的关系结成了好朋友,其中既有汉族人,也有不少维吾尔族人;既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有不少是从其他省市来的外地人,其中就有不少的上海人。
事实上,在阿克苏地区财政局工作的上海人,除了财政局工会主席兼预算科长卢维民同志外,还有副局长季汉江同志。他在当地从事财政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财政”。而且,他在农一师医院担任财务科长的爱人,也是上海人。在我到任后,季汉江同志也曾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使我较快的熟悉了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为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平时的工作过程中,我还结识了同为上海人的地区文化局局长俞大姐、地区物价局局长许珑同志等,他们那种热情开朗、兢兢业业、忠于职守、无私大度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然,结识的朋友中,更多的还是当地人和外省市来的人,他们中既有地委、行署的领导,也有地区各直属机构、各县市的负责同志,还有一些是医院、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不是亲人但又胜似亲人”。他们的那种爱是那么纯朴,他们的那种亲是那么发自肺腑,令人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感受万般情
在阿克苏工作的三年,我曾被许多人、许多事感动过。
地区财校校长薛育才同志,身体一直不好,但他对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情有独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任职期间,地区财校有了较大的发展,他的学生遍布了整个地区并在地区财经战线上发挥着很好的作用。他在我援疆期间不幸逝世后,应财校之邀,受地区财政局党组委托,由我为他致悼词。为了写好悼词,我曾看了他的档案材料,走访了财校的一些领导和他生前的好友,给我的感觉就是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追悼会上,受到大家情绪的感染,我是哽咽着把悼词念完的,回到单位办公室,我还是沉浸在悲伤之中,为他的离世悲痛不已。
结对扶贫也是我们援疆的一项工作。抵达阿克苏以后,经与地区教育部门联系,我们每一位上海援疆干部都确定了一名援助的学生。我资助的学生是一名维吾尔族小姑娘,名叫阿依古丽,当时就读于阿克苏市的一个小学。我曾带着一些学习用品到她家去看望,看到的情况确实让我心酸不已。家庭条件虽然比较差,但她的老师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学习十分用功,成绩非常优秀,还是一个学生干部。由于语言交流不是很顺畅,我和她交谈得不多,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她心灵的纯净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我还和她合过影,相片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影集之中。
“古尔邦节”是维吾尔族兄弟姐妹的一个重大节日,单位也要放假以示庆贺。按照多年形成的惯例,援疆期间,每到这个节日我都会和地区财政局的所有领导以及一些科室的同志到单位里的每一位维吾尔族同志家去贺喜。过程并不复杂,任务也很单一,就是大家团团坐在一起,用一个酒杯按次序喝酒,这家喝完了几杯再换另一家,好几家人家转下来,参与贺喜活动的同仁们也都醺醺然地回家了。
在援疆三年的过程中,23位援疆干部在上海援疆联络组组长、阿克苏地委副书记沈秋余同志的带领下,紧密团结、亲如兄弟、同心同德,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无私奉献,赢得了阿克苏地区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岁月匆匆流逝,三年的援疆生活将一直沉淀在我的记忆里,永不褪色。我想说,我爱那远在万里之外的又一故乡——阿克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