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云南十五载
2017-03-30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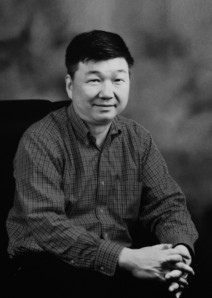
【口述】
方城,1960年5月生。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市政府协作办公室)副局级干部。
口述:方城
采访:周文吉彭军孔令君
整理:孔令君
时间: 2016年5月4日
从1996年6月我结束援藏工作,当年10月调到市政府协作办经济(对口支援)处,1997年1月对口支援处成立,直到2010年10月,我一直参与沪 滇对口支援工作,算来正好15年。再加上我援藏和在新疆工作的经历,心里始终离不开对口支援这件事,有感情。说来你或许不相信,为了搞清楚“对口支援”的 由来,最近我花了150元,从“孔夫子旧书网”上买来了一份文件,是1979年中共中央的52号文件,转批了乌兰夫同志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报告。
这是沪滇对口支援的开头,也是我心中故事的开头。
“对口援滇”的由来
回顾历史,沪滇对口支援,最早可追溯到1979年的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长的乌兰夫首次 提出,国家要“组织内地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历史意义的“对口支援”被第一次确定下来了:“北京支援内蒙,河北支援贵州, 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西藏。”当时的支援,是按照“扬长避短、互利互惠、互相支援、共同发展” 的原则开展的,对援助资金投入上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主要靠发达省市的自觉。上海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受援方认可,中央还在1991年全国对口支援座谈会 上,介绍了上海支援云南、宁夏、新疆、西藏的成功经验。
到了1994年4月,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 发行动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诞生了,提出了“在1994年到2000年七年时间里,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奋斗目标。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1996年9月23日,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第一次在北京召开,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副市长蒋以任、市政府副 秘书长姜光裕代表上海市出席。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重申:“今后五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 到20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贫困地区,是动员全社会力量扶贫的重要举措,各经济发达省市要作为一项政治 任务,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切实抓出成效。要把帮扶任务落实到县(区),落实到企业,明确目标任务,不达到目标不脱钩”。
由此,真正落到实处的对口帮扶才开始。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正式部署了对口支援的“对子”,比如北京帮内蒙古,天津帮甘肃。而上海定下来帮云南。
你可能会问,1979年的方案,是上海对口云南、宁夏两个省区,后来为啥只对口云南了?这里有个故事,听我的老主任谭甦萍讲,1996年对口支援方案调 整时,福建加入进来,从地理位置考虑,应该是“上海帮宁夏、福建帮云南”的,相对更近。可是考虑到沪滇两地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比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 始,结合“三线建设”,上海不少轻纺、机械企业迁到云南,还有数万上海知青赴云南上山下乡,特别是1979年建立了对口支援关系后,两地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上海的13个区、县与云南13个市、地、州对口结对,两地教育、卫生等部门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对口帮扶关系。因此,当国务院有关部门征求上海意见时, 上海就主动提出与云南结对。
由此可见,新时期与“扶贫攻坚”挂钩、对口关系明确的上海与云南的对口帮扶关系,应该从1996年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算起,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援滇开局,我随黄菊访云南
再回到20年前的原点,上海如何行动的?时任市委书记黄菊说得明白:“要举全市之力,把帮扶任务落到实处,用真情回报中西部地区人民长期以来对上海的支援。”
万事开头难,上海用的劲头很实。1996年10月,时任市长徐匡迪、副市长蒋以任率团赴滇,拉开了新时期沪滇对口帮扶的序幕;成立了以副市长蒋以任为组 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姜光裕、市计委副主任杨雄为副组长,由16个部委办局、12个区县领导参加的上海市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市政府驻昆明办事处正式 挂牌;经市编办批准,1997年1月,市政府协作办专门增设了对口支援处,承担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很荣幸,一开始我就成为其中的一员;确定由上海12个区 县分别对口帮扶红河、文山、思茅三地州的22个贫困县;建立了对口帮扶资金;建立会议制度,每年年底召开一次由两地分管领导出席的联席会议,总结当年工 作,布置次年任务;1997年7月2日,我随市协作办周伟民副主任,把精心挑选的首批12名干部送到云南帮扶第一线,开始了一年半的挂职……
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中央发出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号召,但对援助资金方面一直没有具体要求。上海按照“动真情、办实事、见实效”要 求,在全国带头建立了每年2000万元的“对口云南帮扶协作资金”,为此上海专门成立了“资金管理小组”,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姜光裕和市财政局副局长蒋卓庆 担任正副组长。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独立账户,办财务胡依萍担任会计,我还兼任出纳。
派出干部的第二年,1998年6月6日,时任中共上海 市委书记的黄菊率团再次到云南学习考察,检查帮扶工作,这次我随团。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市委书记第一次带队到对口支援地区。四天中,考察团行程千余公里, 从昆明来到红河、文山两州,入村寨访贫问苦,进学校看望师生,到农场考察帮扶项目,亲切接见了援滇干部,并和云南的同志进行了多次座谈交流。
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是在文山县麻栗坡村,黄菊走出村民家时,问村里有没有学校,当听说有一所小学时,就一路上坡,来到只有几间土房的学校,穿着苗 族服装的孩子们一下子围了上来。黄菊和一旁的团市委书记薛潮商量后,对孩子们说,大家要努力学习,一年年读下去,上海将通过“希望工程”,为你们再建一栋 新校舍,并且每年会来看望你们。孩子们听了,高兴极了,一定要和黄菊爷爷合影。我当初做了个有心人,带了个“拍立得”,黄菊在孩子们的簇拥下,照了一张又 一张相片,现场拿到照片的孩子们又奔又跳高兴极了。
二是黄菊在讲话、交流中强调,上海帮扶工作一定要在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云南是帮困扶贫的主力军,上海是“配角”,但我们要争取得“配角奖”。对云南方面提出的要求,特别是红河、思茅和文山的同志提出的要求,回复只有四个 字:“照单全收。”同时要求市里要每年派一个代表团来,检查工作的落实情况,强调“以后无论什么部门、区县的代表团来云南,来之前要有计划,回去要有报 告,决不能做没帮忙反添乱的事情”。
我当年还是一个进办不到两年的“年轻人”,很快接到了“压力山大”的任务——出访第二天晚上,在红 河宾馆会议室里,市领导主持会议,逐条研究云南方面要求,姜光裕秘书长提出了具体要求:“搞个十条。”由于同去的费金森处长打前站先去文山了,起草文件的 任务就落到我身上,我一方面连夜听取、核实云南想法,另一方面反复征询同去的委办领导意见。第二天一早,一份“干货满满”的《工作纪要》形成了,内容包括 加强干部交流和人才培训工作(每年增加100名到上海培训,22名到上海挂职),加大社会帮扶的力度(新增88个温饱试点村、220个卫生所、220个希 望小学),协助做好小额信贷工作(提供5000万元无息贷款),由上海市农委负责援建的红河农业良种基地场从500亩扩大到1000亩,进一步加强两地经 贸合作(每个对口县都要落实一个项目),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加快市场开拓的步伐,积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浦发银行在云南设立分行),进一步发挥好培训中心 的作用,建立健全帮困扶贫工作检查落实的制度等十项任务。后经同去的市委研究室综合处处长俞克明修改、定稿。代表团离开云南前,两地领导再次见证,签署了 首个以代表团名义为协作方的文件:《上海市代表团与云南省关于进一步做好两地对口帮扶协作工作纪要》。
由此,也形成了工作惯例,之后对 口援助的出访、来访都是如此。我统计过,在“九五”期间共形成了八个《工作纪要》,其中联席会议四次,代表团互访四次。“九五”“十五”“十一五”15年 间,共召开了12次联席会议,形成了《上海—云南对口帮扶与经济社会协作“九五”计划纲要》《上海—云南对口帮扶与全面合作“十五”计划纲要》《上海—云 南对口帮扶与经济社会合作“十一五”规划纲要》,两省市领导互访超过20次。
赴滇调研17天行车4000多公里
那年黄菊书记到云南时,充分肯定由上海援滇干部创造的“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进村入户”帮扶方法,亲自把“脱贫示范村”改称为“温饱试点村”。
为了进一步落实黄菊书记的要求,适逢上海援滇干部入滇一周年,同年7月2日至18日,我又一次来到云南,就“温饱试点村”的实施情况开展调研,和援滇干 部联络组常务副组长周振球一起,从昆明出发,在17天时间里,行车4000多公里,从昆明出发,先后到文山、红河、思茅三州市的13个县、19个乡、18 个自然村,分别与省扶贫办、三地州领导座谈,听取了县至乡村各级领导和援滇干部的介绍,走村串户,坐着小板凳与农户面对面交流。
这也是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调研。当年路况不好,面包车一路颠簸,年轻人不怕苦,几乎隔天就要奔赴下一个县。记得有次路遇山洪,桥墩被冲掉了,只能等对面来拖拉机 接;还记得,一次到了乡里正逢停电,于是就点蜡烛开会;还记得,我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鞋掉落到沟里,被水冲走了,陪同的乡干部马上从家里找出了平时舍不 得穿的新皮鞋……
虽然实施“温饱试点村”工作开始才四个多月,可我记住的,不是苦,而是当地农户表现出来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信心,以及增 强了脱贫致富的自豪感。当时村里面刚拿到第一批资金五万元,援滇干部与当地群众创造了许多好方法,广大农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我要脱贫”的积极性。景东县 岔河村通过“五个一工程”建设,使村容、村貌发生了变化,农户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在周边村庄引起了强烈反响。元阳县保山寨村是试点村中最大 的,共有163户,通过新建改建饮水池、新建厕所、修缮道路使全村面貌大为改观。在整个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明确资金总额,乡村干部十分珍惜,一分钱 当作三分钱用,广大农户更是积极投工投料,墨江县孟力里村有一条一公里长的乡村公路要修,预算2.5万元,帮扶资金用于购买炸药、导火索、雷管、水泥等必 需品,而农民投工投料折资超过一万元。村民说得好:“上海人民没忘记咱山乡的老百姓,把温暖送到了家里,扶贫扶到了田间、地角,这确实难得呀,我们再不努 力摆脱贫困,怎对得起上海人民。”调查报告中的建议,也大多是“干货”——比如,建议考虑云南特有的雨季和旱季,提前实施1999年温饱试点村计划;建议 发动全社会力量,展开百家企业(单位),建百家温饱村的活动;建议将上海向云南提供的“5000万元小额信贷”与上海的温饱试点村建设捆绑起来使用,力争 在三年内,在三地州911个贫困行政村中,都有一个自然村实施“温饱试点村”工程等。这些建议受到肯定,姜光裕、周伟民还专门在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
回想起来,印象比较深的,还有“电视收视工程”。治贫先治愚,当时黄菊书记非常重视,要求上海援助的村庄每家每户都要能看得到电视,听得到广播。调查中 我们发现,由于地处山区,居住分散,加上条件限制,18个村庄中只有麻栗坡县歇房村和砚山县以得邑老寨村离乡政府近,装上有线电视,效果好,农户电视机拥 有数也较多;其他一些村采用的是“211”模式(用一个直径为两米的“锅”,接收、发射一套电视节目,辐射半径为一公里),频道单一,效果不好,拥有电视 机的家庭屈指可数,更有四个村收不到有线电视信号。怎样才能让边远山区的老百姓也能看到高品质的“有线电视”呢?当时我、援滇干部与同去的上海广电(集 团)专家沈双林、戴伟民一起反复研究,形成了“卫星接收、电缆传输”村级广播电视站的建设方案,就是通过卫星天线接收信号,经过变频、放大,转成视频信 号,再经调制器、混合器,通过电缆传送到家家户户。它不但能接收六至八套电视节目,而且能通过专用频道传播广播、录像、碟片等,从而为试点村的精神文明建 设提供了基本条件。回沪后,8月10日下午,蒋以任副市长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了汇报,肯定了我们提出的方案,形成了会议纪要。在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在市 政府的会议室里,直接向市领导汇报。会后,上海广电(集团)立即行动,组织精干力量,与上海援建的“温饱试点村”同步建设的“有线广播电视站”,把视频电 缆接到了家家户户,受到热烈欢迎。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温饱试点村的后续故事
“温饱试点村”的走访调 查,让我感怀至今。而后,“试点村”也开始了快速发展模式。由最初实施“五个一工程”(一所村校、一个卫生室、一批沼气池、一批小水窖、一批种植项目), 逐步发展为“推广一个优良品种,培育一批致富带头人,援建一个农贸市场,建设一个科技文化活动室,完善一批公共基础设施”,再发展到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规 划,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推进,先后建设一批温饱试点村、安居温饱试点村、脱贫奔小康试点村、白玉兰扶贫开发重点村,形成递进式对口帮扶模式。“温饱试点 村”重在脱贫,“安居温饱试点村”重在安居,“脱贫奔小康试点村”重在改善“四个基本”条件,“白玉兰扶贫开发重点村”重在改善“四个基本”的基础上发展 产业。
怎样有效地推广援滇干部与当地群众创造出的好经验好方法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结合两地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在会前加开现场经验交流 会,这样可以起到及时总结经验,相互取长补短的作用。在我的印象中一共召开过四次。首次现场会于1998年12月25日在思茅地区景东县召开,现场参观点 选择在由普陀区对口的景东县龙街乡岔河村、景福乡勐令村,想法就是要推广“五个一工程”的经验。第二次是在2002年12月18日,经过六年建设各种类型 的温饱村超过了1000个,达到了1037个。这次现场会变成了总结会表彰会,表彰了六年来涌现出的153个先进集体和18位先进个人,现场参观点设在杨 浦区对口的西盟县中课乡小寨村、窝龙村。考察“安居温饱试点村”建设情况时,从山坡上望去,连片的红砖石棉瓦房层层叠叠,至今历历在目。第三次现场会于 2004年12月25日,移师到了文山州召开,现场考察了松江区对口的邱北县八道哨乡大龙潭村脱贫奔小康示范村和闸北区对口的砚山县盘龙乡奔小康示范村工 程建设情况。第四次是在2007年2月2日沪滇对口帮扶10周年之际,现场会演变成为经验交流会,考察点选择了奉贤区帮扶的石屏县异龙镇六家山村,“白玉 兰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情况令与会代表耳目一新。
现场会的成功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递进式温饱试点村”的经验,也得到各方面的肯定。
1999年4月,云南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通知,推广“上海云南建设温饱试点村的做法和经验”。
2001年5月,中央又一次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市协作办副主任周伟民在小组会上交流发言引起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马凯的重视,夸奖“温饱试点村”的“五个一工程”做得好,希望上海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扩大扶贫成果。
2002年10月,时任副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社《国内内参》登载的记者吴复民写的《上海实行进村入户帮扶云南20万人脱贫》上批示:“上海帮扶云南的做法、成效和经验应予重视并认真总结。”
2004年5月,由世界银行发起的首届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部长级专家圆桌会议上,时任副市长冯国勤作了《上海—云南对口帮扶反贫困案例报告》,“递进式温饱试点村”也被更多人熟知。
对口扶贫成绩单
总有人问我,扶贫了这么多年,为啥贫困人口不见减少,甚至越来越多?实际上,其中有扶贫标准和目标不断调整的因素。20世纪末是以解决“绝对贫困”为目标,而到2020年是要确保所有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一起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20多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将扶贫帮困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先后召开了多次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 扶贫开发,使扶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扶贫政策也不断改进,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 “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精准扶贫”。扶贫的标准也一直在提高,从1986年“绝对贫困标准”的每年206元,到2000年“低收入标准”的每年 865元,到2007年“扶贫标准”每年1067元,随着消费价格指数等相关因素的变化,2009年进一步上调至每年1196元。2011年,又将“新十 年扶贫标准”提高到每年2300元。
上海对口支援的领导机构也经历了多次改变。2003年8月,根据《上海市机构改革方案》,合并了市 政府协作办、市政府接待办、市级机关的沪办工作处等与服务全国有关的职能部门,成立了市合作交流工作党委和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并建立了市国内合作交流工作 联席会议机制。2005年4月,市里又把市对口云南帮扶协作领导小组、市援藏援疆工作领导小组、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领导小组三个小组和上海市国内合作 交流工作联席会议整合起来,成立了上海市合作交流与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常务副市长冯国勤担任正副组长,整个市政府合作交流办 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2010年4月,市委决定将原领导小组更名为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把对口支援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当时组长是时 任市委书记俞正声,第一副组长是市长韩正,三位副组长分别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沈红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和副市长胡延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也扩 大到56个,可谓是级别最高、范围最广。
“九五”开局,上海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市财政总共投入援滇资金1.6亿元。五年来上海对 口的12个区县也积极筹措援滇资金7995万元,其中最多的松江、虹口超过1000万元,最少的也有388万元,加上社会各界捐赠,“九五”累计投入帮扶 资金28169万元,实施帮扶项目1756项,其中,援建“温饱试点村”401个、“扶贫安居村”56个。
“十五”时期帮扶资金投入更 大了。除了继续保留市级“对口云南帮扶协作资金”外,市领导小组每年年初下达《上海对口云南帮扶协作工作任务书》,明确任务,对上海12个对口区县筹措的 帮扶资金提出要求(前三年每年不低于150万元,2004年不低于200万元,2005年要求超过300万元)。2004年4月,上海市党政代表团赴滇考 察,决定增加资金8000万元,支持云南开展“向绝对贫困宣战”,又将迪庆列为上海重点帮扶地区。6月,我随胡雅龙副主任到迪庆调研。通过考察,提出启动 方案,确定嘉定、宝山和上海航空、锦江集团(2+2模式)对口迪庆州三个县,一方面建设各类温饱扶贫项目,帮助老百姓脱贫,另一方面助力“香格里拉”旅游 品牌的建设。2005年市级帮扶资金从2000万元,直接跳到了8500万元。据统计,“十五”期间市级财政投入达到了2.61亿元,12个区县实际投入 达到16322万元,加上社会捐赠,累计在滇投入无偿帮扶资金73209万元,实施对口帮扶项目1700个,其中包括以建设“递进式温饱村”为主的“整村 推进”项目763个。
“十一五”开年(2006年),市领导小组决定将原来分开筹集的援藏、援疆、援滇、援三峡资金进行全面整合,同时 把区县筹资金也收上来,放在一个平台上,建立了每年递增10%的“上海市合作交流专项资金”,年度计划报市领导小组审定后,形成《对口支援项目资金安排方 案》,由上海各对口区来具体操作。这是一个大跨越,不光解决了资金筹措难题,同时也解决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工程。我们经过摸底、统计、分析,提出了2006 年的资金总盘子31512万元,其中,核定援滇资金11580万元,占到了总资金的三分之一。“十一五”的成绩单更加出彩,连续五年以10%的速度稳定增 长,市区两级财政筹措的援助资金达到了72360万元。加上社会各界筹措的资金,“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援助的资金85500万元,实施帮扶项目1657 个,含整村推进项目1099个。

进村调研
另一张出彩的成绩单是“人口较少民族帮扶工作”。2005年5月,中央召开民族工作会议后,在两地民(宗)委的努力下,上海又率先把帮扶人口较少民族—— 德昂族发展纳入了“十一五”沪滇合作计划,形成了“4+1”的沪滇对口帮扶模式。2006—2010年,上海市对聚居在德宏、临沧、保山三州市的80个德 昂族自然村全面实施帮扶,累计投入资金3689万元,实施457个帮扶项目,1.78万德昂族群众整体脱贫。另外,还针对性地开展苦聪人帮扶,2006— 2008年共投入资金1806万元,在苦聪人集聚的普洱市恩乐镇、九甲乡、者东镇21个自然村实施整村推进建设。2008年春节前,上海援建的镇沅县恩乐 镇大平掌新村落成,50户200名苦聪人搬入新居。上海还主动参与红河州金平县莽人整体脱贫攻坚活动,承接了雷公打牛村易地搬迁任务,2009年6 月,43户195名莽人高高兴兴迁入牛场坪安置点。上海帮扶出成绩,被国家民委树为民族团结进步的先进典型。
2009年10月,我又一 次来到了云南,这是我15年中最后一次。这次是应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之邀,跟随林湘书记到怒江州实地考察独龙族帮扶工作。车辆早上七点从贡山县城出 发,泥泞弯曲的石头路上一直有雪水流过,90多公里路程足足走了八个小时,到下午三点才进入独龙江。横跨东岸的高黎贡山海拔超过3000米,每年冬春季节 大雪封山,独龙江乡被封闭隔绝长达半年之久。许多独龙族群众还居住在简陋破旧的茅草房、木头房或篱笆房里,而且人畜混居,不少家庭全部家当不值500元, 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刚过800元,多数老百姓穿的衣服都是外面捐赠的。“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帮扶一个独龙江乡,实质上解决一个民族的发展问 题”,作为中央确定的东西协作结对省市,上海积极参与帮扶怒江独龙族加快发展,时机上成熟,操作上可行,林湘书记当场“拍板”,要把独龙江乡纳入上海帮 扶。当时我的感触很深,云南省内还有这么多地方如此贫困,上海对口帮扶工作还远没完成,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更理解了黄菊同志当初所要求“照单全收” 的真正用意。要在2020年让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同时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需要我们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努力!2009年12月,沪滇帮扶第十一次联席会 议确定,从2010年起,将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独龙族列为上海帮扶对象。
2010年10月,为全面加强对口支援工作的组织协调工作, 根据市编办方案,对口支援处拆分为一处和二处,人员编制也从8人扩大到14人。对口支援一处以援疆、援三峡、援黔等工作为主;对口支援二处以援藏、援滇、 援青等工作为主。我被安排在对口支援一处工作,随后工作调整,我离开了工作近15年的援滇工作岗位。2012年9月,我又一次响应组织的召唤,来到祖国的 西部边陲新疆工作,直接加入到建设边疆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