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雪域高原
2017-03-06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口述】张伟,1971年9月生。现任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2010年至2013年,为上海市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中共江孜县县委书记。
口述:张伟
采访:刘世炎 冯谷兰
整理:陈福如 刘世炎
时间:2014年2月27日
我们第六批上海援藏干部的选拔是个人自愿报名和组织委派相结合,2010年6月份从上海出发来到西藏的。我对西藏没有陌生感和心理障碍,在闵行区工作期间我曾经两次进过藏,因为在办公室工作,2004年和区领导一起去慰问援藏干部去过一次,2008年去看望我以前工作单位一个在西藏挂职的副镇长,而且闵行区一直对口西藏江孜县,我做联系工作,和江孜县一直有联系,江孜县的很多干部我都认识,所以我对西藏没有陌生感。到莘庄镇工作以后,我们莘庄镇的一个副镇长在江孜县挂职县委副书记,联系也比较多,他们每年都会过来和大家一起交流等,所以那些人也都熟悉,没有什么陌生感。
努力适应,加快融入角色
我到西藏担任江孜县委书记,跟我以前的工作有比较大的区别。一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原地区,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一个宗教地区,并且是我们祖国的边境,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各方面都比较特殊。应该说,整个西藏,给我的感觉是,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还是欠发达地区,幅员辽阔,12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虽然只有300万人口,却是少数民族和宗教比较集中的地方,工作重点同内地差别比较大。作为上海的援藏干部,还担任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各方面的责任压力都比较大。我们有着双重职能,一个是要把上海交给我们的援藏任务做好,另外一个作为县委书记,要把当地的工作做好,就是说带着双重的责任过去的。另外,那个地方毕竟还是一个高海拔地区,从低海拔到我们县的4100米,说和在平原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不可能的。我也说实话,有一个生理适应的过程,还有一个生活适应的过程,再接下来才能够融入当地的工作,如果前面两个克服不了就没法工作,关键是身体能否适应高原。通常,我们从上海去西藏旅游,或者是上海的领导到西藏去慰问援藏干部,进藏的时间大部分安排在每年的6至8月份,因为6至8月份是西藏最好的时候,气候比较好,绿化、气压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西藏真正比较艰苦的时期是在一年的两头。每年一过10月西藏的气候条件马上就变差,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年的4月底,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我的感觉是,高原环境对于自己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毕竟还是三年,把三年熬过来也就过来了,我比较佩服的是当地的干部,他们从小到大都在那里,还有很多长期进藏的汉族干部,他们可能要待几十年,他们的子女长期也在那里,真正辛苦的是他们,我们三年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过程,怎么去适应好这个地方,才能谈怎么样开展工作。
扎实调研,推进援藏工程
我们第六批援藏工作时间是三年,2010年的6月份正式进藏,我是5月份进去的。到2013年6月份,实际上是跨了四个年头。上海的援藏任务,从工作安排上来说,一般第一年进去以后,先要搞调研,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我们这一批上海援建要做什么,第一年的半年时间基本上是在调研和确定援建任务。最后一个半年,就是2013年,我们是6月份回来的,2013年那个半年基本上是在搞项目收尾、审计工作,和新一批援藏干部交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真正在那边能够做项目的只有两年,就是2011年全年和2012年全年。

羊湖春色
西藏有一个特殊情况,因为海拔比较高,每年的施工工期最多只有六个月,不像在上海全年都可以施工,基本上没有太恶劣的天气,而西藏就是每年的4月15日至10月15日之间,只有六个月的工期,真正能够施工的其实也只有五个月。4月15日开始做开工准备,10月1日后马上要做停工的安排,真正就是5至9月可以正常施工,两年加起来也只有10个月。我们援藏三年,真正能干活的就是这10个月。工期非常紧张,所以每个时间点都要踩准。第一个半年的调研,确定项目后要报上海,上海决定了以后要和自治区一起确定,然后我们还要做准备。项目管理很严格,要报建、立项,才能开工。很多项目必须要在第一年的5月份开工,不然的话援藏任务就会完不成。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以前接触不到,到了那儿一了解情况,觉得还是比较紧张,一定要把每个时间节点计划好,才能完成上海交给我们的援建任务,不然的话是很麻烦的。所以项目这块我们还是排了一些计划,抓紧时间,确定的项目马上开工,特别是一些基本建设项目。当然,援藏也不单是基本建设项目,但基本建设项目如果做不好的话,你的援藏工作也就很难说做好了。所以,虽然援藏是三年,但是真正能够干活的时间并不长,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三年能干很多的事情,其实干不了很多事情。
科学规划,发挥最大效益
我们县的援藏项目是22个,实际总投资是1.28亿元。在这些项目中,从项目的投资方向来看,实际上我们主要考虑投向了三个方面,这是最能发挥援藏资金产生社会效益的地方。
一是新农村建设。江孜这个地方城镇化的程度很低,虽然在历史上号称西藏的第三大城市,拉萨、日喀则后就是江孜。现在江孜县城的规模并不算很大,我们建成的城区只有8平方公里,县城有近3万人口,在西藏已经算是很大的地方。我们这个县总共是7万人口,3800平方公里。我们开展的第一个项目是新农村建设,主要是考虑中央和上海市对于援藏工作的总体定位,就是“向农牧区倾斜,向农牧民倾斜”的两个倾斜的要求,主要是农牧区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农牧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包括开发一些荒地,搞一些水利设施,乡村道路的改建,农村综合环境的整治,还有一些就是安居工程。虽然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上,安居工程占整个上海对江孜的投资比例不算很大,大概在12%—13%,但是我们觉得安居工程做下来,是西藏农牧民感受最深的项目。安居工程从中央对西藏的援助来说有一个普遍的政策,就是国家给你补贴,自己再出点钱修房子。国家对西藏还有一个政策就是“沿路”建房,就是补贴国道边上造房子。但是西藏大部分的农牧民,可能有1/3的人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一是在山沟,不在路边;二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拿不出这笔钱去建房子。我们上海的援建项目资金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可以对国家投资的安居工程拾遗补缺。我们重点解决的就是贫困户的住房问题,将集中点建设和分散户补贴相结合,对于居住相对集中而且周边有土地资源和水电优势的贫困户,安排施工队集中新建,而对居住较为分散且无集中新建条件的贫困户发放现金补贴以善居住条件,尽量扩大贫困户受益规模。将贫困户家庭情况与建设补贴标准相结合,就是根据贫困户家庭困难情况、人口数量多少,合理安排援藏资金,将安居工程建房面积和补贴标准分为上中下三档分层实施。我们的安居工程补贴的标准要比国家确定的标准适当高一点,老百姓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就由我们上海来出。我们不是直接给他们钱,是通过项目资金把它建好,帮他造,自己出一部分我们再补贴一部分,但是标准肯定比国家的标准要稍微低一点。为什么?其他享受国家政策的人,比如建了100平方米的房子,他自己拿钱,我们解决困难户,虽然说补贴标准高,但是建房的标准比国家的标准还稍微低一点,比如面积上稍微小一点,不然的话大家心里不平衡。但是这样他们也很欢迎,通过安居工程能够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这是新农村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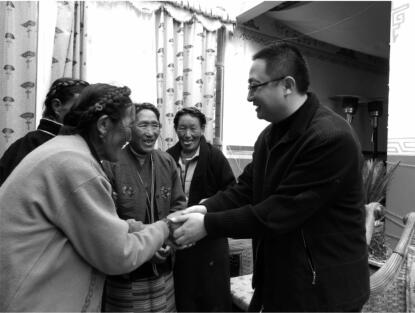
慰问群众
二是新城镇建设。江孜算是一个人口相对比较集聚、具有县城规模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城镇建设方面投入了不少的资金,搞了一些项目。江孜历史上是西藏的第三大城市,它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国务院确定的,历史比较悠久。江孜这个地方在旧西藏时是出贵族的,旧西藏三大贵族为喇嘛、政府官员和农奴主,江孜在历史上是出这些人的。
《红河谷》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江孜。我们去了以后,包括上海联络组、上海合作交流办,给我们提出改善历史文化名城江孜古城新面貌的要求,希望把历史文化名城的效益发挥出来,发展旅游业,增加当地的收入。在历史文化名城的打造方面江孜是有条件的,但我们去的时候,总体感觉江孜和历史文化名城不太匹配,比较脏、乱,城市管理不到位。应该说江孜也是上海援建的五个县的重点,援建资金是最多的,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管理方面。
我以前在基层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我所在的闵行两个镇,虹桥镇、莘庄镇都是一个城市化建设地区,以前是农村,后来逐步城市化了。所以,我在城市城镇管理方面还是积累了一点经验,到江孜正好用得上。我们在管理上花的钱不多,在新城镇的投入上,管理只占了1/5,其他的还都是硬件投入,比如店招店牌的整治、道路设施的改建、一些环卫设施等各个方面的投入,再加上管理费用。我们组建了一个江孜的城镇管理中心,实行网格化的管理,分了几个组,建立城管队伍。我们后来搞了一点奖励,分片包干,环卫工以前扫地的只有300元,我们后来增加到500元,只要考核下来这个地扫得干净,没问题,500元一个月,他们也很高兴,很开心。因为西藏的整体收入不算很高,到2012年为止,整个自治区是4600元,我们江孜大概是在6200元。不管是从管理、服务、宣传还是执法方面都加强了,西藏的老百姓还是比较纯朴的,他们也比较自觉,你跟他说不行、不能做,他们知道不行就不做,还是比较服从管理的。应该说从第二年开始,江孜的面貌还是有了一定的变化,我觉得这样做是比较值得的。
三是对社会事业和党建方面的援助。包括文体设施、医院、有线电视这些方面的投入。还有就是西藏的党建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那里是一个宗教地区,基本上是全民信教,虽然可能教派不一样。我觉得基层党建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党建方面我们投入了不少钱,我们觉得关键的问题不是靠我们去援助,关键问题要靠他们自己,我们援助的工作是暂时的,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能够有观念上的转变,能够认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输血和造血的问题,靠输血没有什么用的,这是短期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提高发展能力,才能改变西藏的面貌。所以说从党建方面来说,从人才的一些培训等方面,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而且做下来大家的感觉也比较好。西藏的教育是很普及的,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可能西藏这个地方的孩子很多不上学,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那边的义务教育率可以达到99%以上,而且那边的措施还比较严格,不上学要抓的。这是因为援建,西藏的上学是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用品,全是国家包掉,人到学校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花钱,教育还是非常普及的。但是他们那边义务教育结束以后,就会有孩子读书读得好但可能读不下去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地人均年收入只有4000多元,好的只有6000多元,比如家里一个孩子读高中一个读初中,这个家没有劳动力了,没有劳动力赚钱,又要负担这些孩子读书怎么办,很多孩子就是读得好也不读,要回家干活去。我们闵行区领导非常支持帮扶学生,我们在的那两年共扶持了将近100个孩子,有高中的有大学的,每个孩子最高9000元,最低也要四五千元。西藏的大学生如果在内地读,这四年就没钱回家了,家里给他钱吃饭、开销已经差不多,再回来路费什么的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再加1000元是路费,就是你能够读得好,还能回来看看父母,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的。
总之,我觉得援藏项目一定要有针对性,能实实在在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国家政策上是覆盖不到的,比如安居工程、教育工程,总归有一些政策的局限,但是我们援藏项目能够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我觉得我们援藏,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合适、比较妥当的。
情系高原,自觉历练人生
我还是说个人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一是我们对西藏千万不能“怕”。比如说有人形容高原怎么怎么可怕,蛮荒之地啊,不大开放的地方啊,其实那边环境比我们想象中好一些。1994年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开始对口支援西藏,从1995年开始,到今年是第20年,经过20年的援建,西藏各个方面和内地的交流比较多,各方面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我2004年和2008年进藏,和我2010年去援藏,都很有感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04年我去西藏,从拉萨机场开到拉萨市要两个半小时,因为拉萨机场在比较远的地方,而且它的路是盘山公路,很不好开。2008年去的时候,从拉萨机场开到拉萨市,需要一个半小时,因为有了一个穿山隧道。我们去了以后,到2011年,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建成了西藏第一条高速公路,从拉萨机场到拉萨市区只要45分钟,这就是变化。西藏的生活条件也好,工作环境也好,自然条件等每年都在改善。以前西藏的绿化不是很多,我们每次援藏都在搞,中央都是支持搞环境建设,绿色多了代表氧气多了,唯一不能改变的是海拔,别的自然条件还是慢慢在改变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怕,心理上先承受不了,那么生理上就会承受不了。这个高原反应很怪的,越怕越厉害,稍微放松一点、平衡一点就会好一点,心态很重要。人基本的生理条件,每个人都不一样,高原反应可能更多的是看你血液里的血红蛋白的带氧能力,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不能怕,我们后来都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西藏不管怎么样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城市的建设啊,住宿条件、饮食条件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好,你要怕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做不好这个工作。
第二是不能当“救世主”。到了西藏以后,不是说我们援藏干部就能代替一切,你不是救世主,你是帮助西藏当地干部群众来提高发展水平的,只靠我们几个援藏干部去干,干得了吗?要带动他们一起去做,一定要融入当地,融入他们的工作,融入他们的习惯,融入他们工作的方式方法,我觉得都要融入,才能做好事情。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记住,不仅是做项目要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其他的事情都是要依靠当地。
三是不能有“优越感”。我自己的看法是,作为援藏干部,感觉上在整个西藏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他们非常尊重我们,大家也比较融洽。为什么呢?毕竟援藏干部给当地带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带来了资金带来了项目,而且援藏资金我刚才说了比较灵活,能够解决当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是比较受欢迎的。所以援藏干部能受到比较大的尊重,特别是我们藏族的干部群众比较纯朴,他们会有一种发自内心地对我们党、对我们援藏干部、对我们援藏工作的感恩。但是我刚刚说了,我们只去三年,当地的很多干部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他们的工作家庭生活是在当地的。我觉得除了我们援藏工作要依靠当地干部以外,还要处理好和当地干部的关系,特别是和长期进藏干部的关系,大家都是汉族干部,援藏干部不能有“优越感”,援藏干部受尊重以后不能飘飘然,不要觉得你可以指挥一切,你带钱带项目来了,要想想这个钱和项目是谁给你的?日常工作中一定要依靠当地的干部,援藏干部要跟当地干部处理好关系。不然的话,会给我们的援藏工作带来一些阻力。
三年援藏,我觉得是一段很不错的人生阅历,除了对父母对家庭对妻儿有亏欠,我们在思想修养、政治觉悟和作风素质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驾驭全局、协调各方、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