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洒雪域
2017-03-24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口述】许一新,1956年1月生。现任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1995年至1998年,为上海市第一批援藏干部,担任中共定日县县委书记。
口述:许一新
采访:谢黎萍 黄啸 周炯
整理:黄啸
时间:2014年2月12日
1995年5月17日,我作为上海49位援藏干部之一,响应中央号召,毅然惜别家乡和亲人,来到雪域高原,一干就是三年。
1994年,中央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改变了以往援藏的方式,采取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新形式。分片负责,就是承担支援任务的省市分片负责西藏的一个地区。当时确定了15个支援的省市。对口支援,则是具体到县,上海对口四个县,比如确定我担任定日县委书记,就由我原本所在的松江牵头四个区派出干部进行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就是一批干部进藏工作三年,期满后回来,再换一批去。
当时,中央广泛地宣传孔繁森的事迹,以此来推动全国的援藏工作。孔繁森两次进藏,代表了老进藏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当时,我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学习孔繁森座谈会,听了他的事迹后很受感动。我们很多同志就在孔繁森精神的感召下,主动报名参加援藏,有的甚至以写血书的形式来表达决心。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组织选派,成为第一批援藏干部。如今一晃已19年过去了,至今回忆起来,不少难忘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经受考验
要去的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在哪里?当年我是在地图上找到它的。去了以后我才实地了解到,定日县地处珠穆朗玛峰的北麓,南麓是尼泊尔,它是一个农牧大县。整个区域面积有两个上海那么大,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共是13970平方公里,21个乡镇,182个行政村。定日还是一个边境大县,跟尼泊尔接壤的边境线有180多公里。
进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遽然面对的高原恶劣自然和生活环境。西藏地区的含氧量是平原的三分之二,去过的人都知道,一到西藏就会有高原反应。定日的海拔很高,平均是4500米,相当于50个佘山那么高。我常说定日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日照光线很强,有的援藏干部回沪以后脸上的“高原红”成了永久的纪念。在这样的高原缺氧环境下,人会很难受,像生重病一样。有人说,援藏干部一辈子的药,会在这三年里吃完。我算意志力比较强的,还是吃了不少保心丸。脑袋胀痛难以入睡时,就用两条毛巾连起来把脑袋扎紧。上山不能跑,下车不能跳,晚上枕头抬得高,最关键是要小心得感冒,一感冒就可能会引起肺气肿。我还有两句顺口溜叫做:干巴巴的气候不下雨,光秃秃的山头不长草。当地日照时间长,非常干燥,雨水就格外珍贵,看到下雨,我会情不自禁冲进雨中淋一下,感觉很好。山是光秃秃的,少有植被,经常会有石头滚落到道路上,所以在西藏很容易出交通事故。冬天气温可达到零下二十几度,晚上要把牙膏放进被窝里,不然第二天就挤不出来。所以,恶劣的自然环境便造成了艰苦的生活环境。米饭在高压锅里蒸出来,也才有八分熟,尤其初到定日没蔬菜吃,有时到日喀则出公差时顺道捎来。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们自己想办法,从上海寄来菜种,搭建起大棚,总算根本上解决了吃菜难的问题。这个大棚一直到现在援藏干部还在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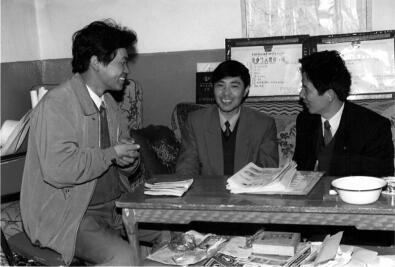
许一新(中)在基层调研
西藏基本上是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藏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藏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饮食起居、风俗习惯上与汉民族有很大的差异。到基层尤其是农牧区去,存在巨大的语言交流障碍。县委班子开会,我要求都能讲普通话(当地藏族领导干部一般都能讲),这样就不会造成他们讲藏语我们听不懂,我们讲上海话他们听不懂的局面。在藏工作期间,必须得时刻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并适应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生活饮食方式,还得学会简单的交际语言。
定日县是一个与尼泊尔接壤的边境大县,又是1959年达赖叛乱时的重灾区,政治环境比较复杂。我们那年去的时候,达赖分裂集团正在推进“和平挺进”西藏的计划,而后又制造班禅转世灵童事件,阴谋失败后又从所谓“非暴力斗争”转向“暴力斗争”。对此,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和日喀则地委的领导下,守土有责,积极应对,组织也给援藏干部配备了最先进的手枪用以防身自卫。
进藏起始,给我强烈的“刺激”是:西藏苦是次要的,最最严峻的问题是恶劣自然环境对人生理的伤害考验、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人心理的考验。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工作,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保持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才能去拼搏奉献。
为民情怀
有人说,援藏干部在西藏,即使不干任何事,待着也是一种奉献。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全面的。我们去都是担起责任肩膀的,组织派你去,如果在三年里,没有给当地带来发展进步,没有给藏族同胞带来收入增长,是说不过去的。而且,身临其境,会越发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工作重任,内心深处会升腾起一种强烈的为民情怀。
定日县是西藏的贫困县之一,而全县最穷的乡就是尼夏乡。我第一次到尼夏乡,受到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当地的房子都是泥堆成的,墙上还敲了很多牛马粪。因为,当地很少有木材,取暖烧的都是这些牛马粪,甚至有的农户是和牛羊混居在一起的。我当时见到这个情景,拿出了身上携带的650元分送给几户最贫困的人家,却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居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随同的藏族干部就对他们说,许书记给的这些钱可以买多少酥油,买多少奶茶,还有青稞酒。他们听完,居然跪了下来,我眼泪也就止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尼夏乡的自然条件实在太过于恶劣,种下去的青稞,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哪里来的收成?于是我和县委一班人决定,尼夏乡要从根本上脱贫致富,需要进行整体搬迁。接着,我们就在其临近的长所乡搞水利建设,造房子,挖水渠,开荒地。每所房子补贴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也是笔挺大的钱了。有了水有了地,便可以种树苗和青稞了。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就动员尼夏乡的居民搬出来。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开始的动员工作很艰难。因为,那些农牧民觉得世世代代在这里,不愿意搬离老家故土。为此,我们就让党员干部带头搬。一年后,再让其他农牧民去长所实地查看。当他们发现长所与尼夏的生活条件相比,实在好太多了,这才陆陆续续搬出来。2002年,我带队慰问后续的援藏干部,又一次去了定日,还专门看望了尼夏乡的乡亲。一位老妈妈还认得出我来,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连说谢谢。我告诉她,不要谢我,你们日子过好了,我们也很开心。
当时的定日县城,也就一公里长,我们刚去的时候,没有一条水泥路,也没有一条柏油马路。信息也都不通,打电话要到邮电局,通过卫星,有时候给家里打电话,才接通就断了,话都讲不上一句,心情特别难受。为此,我们就想制定一个县城建设规划,于是,我请了上海松江建设局的规划设计专家来定日勘察搞规划,又不遗余力积极筹措资金,沿着县城的协格尔河两边进行建设。把原来一条一公里长的沙土路改建为柏油马路,在政府大楼前面,建了一条水泥路,逐步发展县城里的集市和商业娱乐设施。这一规划为以后县城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值得欣慰的是此后的几批援藏干部都没有折腾,坚定不移实施这个规划,使县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珠峰是定日县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每年都有很多国内外游客前往。但是,此前珠峰的旅游收入,都要上缴到自治区旅游局的。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不合理,因为旅游资源是定日地方上的,为此,我和县长专门去自治区旅游局进行协调。比较幸运的是,当时的旅游局局长汤正琪是松江人,所以,商谈得很融洽,同意把这项旅游税收划归定日县。紧接着,我们又成立珠峰经营公司,搞住宿小宾馆,搞物资供应点,组织藏民牦牛队为中外游客提供服务,以此增加藏族老百姓收入,同时县级地方财政的收入也增加了。我们刚去的时候,整个县一年的税收才24万,而我们临走时,已经达到了246万,贫困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定日县被评为全自治区农牧业先进县。

乡间小道
援藏办实事最关键的是筹措资金。我们第一批去的时候,和以后几批不一样。当时,我们的资金都是靠自己筹措的。我在定日三年,和援藏同伴们一共筹措了650万元。在来西藏前,我在松江叶榭镇担任党委书记,当地不少企业都是我帮助引进建成的,所以,我就到这些企业去拉赞助。我还曾从时任静安区副区长的张国洪同志那里筹措了40万元,用于建设定日希望小学。此外,我们还积极争取财政扶贫资金。当时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杨晓渡同志,也是上海的老进藏干部,我经常去他那里寻求支持。筹措到的资金全部用在定日扶贫开发上,由此也欠了不少“人情债”。三年援藏下来,我们认为,依靠个人筹措援藏资金的方法仅是权宜之计,于是,我们第一批援藏干部总领队徐麟牵头主动向市委打报告,希望市里能够统一解决资金问题。我们的意见很快被采纳,从第二批起,援藏资金纳入市里和各区县统筹,这样对口支援就有了资金的保障。
另外,我们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重视政法工作、维护边境稳定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应有努力,情况大为改观。
在定日,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抗击雪灾。1995年底,也就是我们去的那年年底,西藏地区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雪。而我正好在聂拉木县的樟木慰问边防部队。与我同去的还有另一位援藏干部和县公安局长。回来途中,天降大雪,一下子就把道路封了,此时已无回头路。但我想这么大的雪灾,如果县委书记不在定日现场,就是失职,我必须要尽快赶回去。所以,我们只好靠两只脚走路。其过程非常惊险,路上还遇到了因雪灾而冻死的武警战士。见此情景,当地的向导也害怕,不敢继续前行,但在我们劝说下,总算领着我们继续向前走。凭着体力和意志力在雪地里走了大约六七个小时,当走到聂拉木县城时已经是晚上了。看到前面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后,人就瘫倒下来,等醒来后,发现自己已躺在了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我们依仗着铲雪机,在一米多厚的积雪中,开出一条道路,历时一天多,总算赶回了定日。回去以后,我马上紧急部署抗灾救援工作,奔赴抗灾第一线。自治区副主席杨松也第一时间赶到县里指导救灾行动,对我们能最大限度减少人畜伤亡给予了充分肯定。
真挚感悟
三年援藏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所有的收获,总结为这么几句话:心灵的净化,境界的升华,为民情怀的强化,对国情了解的深化,能亲身为西藏的建设、为藏族同胞的民生福祉作点奉献,至今想起来,也深感自豪。
在西藏的时候,我时常用写文章的方式来滋养自己。其实刚进藏时,倒没有考虑过写东西。但每到晚上,特别是冬天,连水力发电都没有的时候,面对的只有一张床、一盏灯、一个取暖烤火的烟囱,闲下来不出门的时候,做什么?靠打牌打发,久而久之也乏味了。于是,我就用自己的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记录下来,不少文章在《西藏文学》上得到刊发。在我回沪数年后,将这些对西藏同胞情真意切、对西藏生活富有质感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之为《情洒雪域》。回沪以后依旧保持着读书学习和记录心得的习惯,去年两本散文集相继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现在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与藏族同胞打成一片的情形。来到农牧民家里,他们总是非常热情,半斤多的青稞酒就端到了你面前,那怎么办呢?只能喝。你喝了,农牧民就觉得你“本不拉”(藏语),这当官的可以,没有架子,老百姓的信任度就是这样来的。有时,你不喝,藏族姑娘在边上一根针一下子就戳过来了,这就叫友情。酥油茶倒上来,哪怕它时间放久了有点变质,可是你“咕咚咕咚”必须喝下去。开春以后,乡野搭起帐篷来,我们援藏干部们一块儿钻进去,与藏族同胞说在一起、乐在一起,吃糌粑和生的风干肉,不能说不习惯,民族之间的情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那个时候工作作风真的是既朴实又扎实。工作中,也得到不少当地藏族干部和老进藏汉族干部的指教,“扎西德勒”的问候语时时嵌入心田。总之,这段援藏经历始终伴随和激励着我在回沪后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乐于奉献。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西藏的土地和人民真好,在西藏工作和生活虽然是短暂的,但人生的体味是浓烈的,这片高原厚土施予我的宽阔宽厚宽容宽松,终身受益,终身享用,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