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7月28日
2016-08-18 作者:余前春余前春 宾夕法尼亚大学
(听闻上海在进行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课题,远在美国的余前春不禁 感慨万千,由于条件受限,课题组未能对其进行口述采访,因此,余前春将其在唐山抗震救灾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书写成文,以纪念在唐山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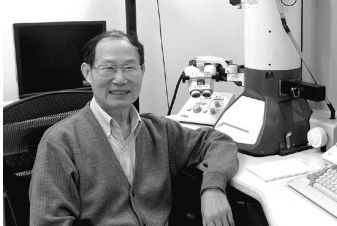
余前春,1975 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并留校任助教。1980 年考取教育部首批赴美博士研究生。1987 年 7 月获马里兰大学医科哲学博士。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爱博生癌症研究所细胞学实验室主任、爱博生癌症中心组织病理学实验室主任。1999 年至今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1976 年 7 月,作为第一批医疗队员赴唐山抗震救灾。
7月28日难忘的日子!再过三个月,就是唐山大地震整整四十年了。我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那一年(1975年)的同一天,恰遇上海暴雨成灾。那天中午,学校在大礼堂为毕业班放电影,突然闪电雷鸣,倾盆大雨疯狂地泻下来,大礼堂里顿时变得一片漆黑。时间不长,校门口的重庆南路上就水深过膝。我从未见过这等奇观,便涉水走到淮海路去观奇。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半淹在水中,平日车水马龙的淮海路成了名副其实的小河浜。
第二年(1976年)的7月28日,唐山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那段时间我正在瑞金医院病理科做住院医生。中午时分我接到医学院的通知,要求我回院本部去参加“紧急会议”,内容就是组织救灾医疗队,前往灾区抢救灾民。上海市卫生局为大队,由卫生局何秋澄担任大队长。我们医学院为一个医疗中队,由李春郊担任总支书记,每个附属医院为两个小队,由我临时负责中队部的文书工作,并兼任内科医生,配合高年资医师立即开始工作。当晚我睡在医学院办公室的电话旁,随时统计、汇总各附属医院送来的医疗队名单及设备,写成报告,连夜送交市委,半夜又和后勤部门赶到市里领取压缩饼干和长大衣。说来奇怪,当时正是夏天。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需要过冬的棉大衣。等我们最终到了目的地,才知道华北地区即使在夏天也需要棉衣。
7月29日凌晨时分,我们医学院系统的一百多名医护人员由上海北站出发,向北驰去。那情景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说心里话,当时我是有一去不复返的思想准备的,所以我特地不告诉远在老家的祖母和父母亲,怕他们担忧。
我们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地震的中心在哪里,只知道在河北省。差不多火车过了徐州,才从列车广播中知道震中是唐山、丰南一带。7月30日下午,我们到达天津附近的杨村车站。因为天津到唐山之间的铁路已被地震破坏,我们只好赶到杨村机场,临时改乘军用飞机前往地震灾区。听说要坐飞机,我心里忽然兴奋起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飞机,别人紧张,我却感到新奇。小时候在汉中老家,我每每看着天上的飞机胡思乱想,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造一架“铜飞机”,坐在它的背上,飞上天去。我那时只骑过黄牛和山羊,以为飞机也是要骑的,不知道人应该坐到飞机“肚子里”;我还以为飞机都是铜做的,因为铜在乡间颇为值钱。小伙伴们取笑我,送我一个颇带贬意的外号“铜飞机”。谁能料到,20年之后我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坐到了飞机“肚子里”!临上飞机前人们警告说,唐山的供水系统已经被毁,没有水喝,要尽量带些水去。机场跑道的一头有个临时挖掘的水坑,我便用随带的烧饭锅盛了一锅,小心翼翼地端上飞机。那是一架苏制的安-24飞机,座位不多。等我进了机舱,别人已经将座位占满。我因为打水迟到了,只好坐在过道里。飞机一起飞,半锅水就洒了。
到达唐山机场时,已经是傍晚。只见到处一片混乱,到处是临时帐篷,到处是救灾人员和大卡车。上海医疗队的队长是刚刚“解放”不久的何秋澄老先生。陈永贵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的帐篷就设在上海市医疗大队部的附近。
我们向大队部报到后,被告知第二天去郊区的丰润县,可是谁也不知道丰润在哪里,也没有地图可以查阅。经过在火车和飞机上两天两夜的颠簸,人已经疲惫不堪;领了帐篷,吃两块压缩饼干,就抓紧时间休息。许多上海人是第一次出远门,更多的人从未睡过帐篷,总是难以入眠。我以前曾经睡过几年帐篷,毫不陌生,也来不及去想明天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很快就进入梦乡了。
午夜时分,我们忽然从梦中被人叫醒,命令迅速离开。原因是我们睡觉的那块土地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就会沉陷,必须尽快离开。“地陷”这个可怕的字眼,我是听说过的。但没想到会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巧。还没给灾区人民服务,自己就先葬身地腹,岂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大伙儿如惊弓之鸟,拆除帐篷,匆忙上车,催促司机赶紧发动,尽快逃离那随时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不巧分配给我们的司机,也是临时从外地调遣来的,对唐山地区的道路根本不熟,大家边开边问,提心吊胆。有一段路正好经过重灾区唐山市路南区,到处是断壁残墙,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废墟;时而晨风吹过,浓郁的腐尸气味便扑鼻而来。随处都能看到:部队的官兵通宵达旦抢救伤员,路旁临时搭起来的简易帐篷,衣衫不整的灾民,也有倒塌的楼层上挂着的遇难者。差不多凌晨时分,我们的车队在废墟之间爬行,终于穿过了闹哄哄的唐山市区。
盛夏时节冀东平原的清晨,凉风习习,将我的睡意完全赶跑了。晨曦之中,公路两旁都是笔挺的白桦树。地震之后,路面损伤很厉害;我们的车队朝着丰润慢腾腾地开着,不时有老乡赶着马车从边上擦过,一甩马鞭儿,那清脆的鞭响在平原上传得老远老远。我生平第一次来到华北平原,颇感新奇。脑海里一会泛出电影《青松岭》里“长鞭一甩叭叭地响”那情景,一会又极力在公路两旁寻找“青纱帐”,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丰润。我伸伸懒腰,准备收拾东西下车。忽然听到有人在地上大声吼叫:“不准停车,马上开走!”司机不敢怠慢,一踩油门将车开出几十米方才停下来。回头一看,原来我们的车刚好停在一堵摇摇欲塌的残墙脚下。后来那堵墙在余震发生时轰然倒唐山发生大地震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慰问电下了。
跳下汽车,我们就在县医院门口的那块土地上,搭起了抗震篷,建起了上海医疗队的“抗震医院”,接收了唐山转来的第一批伤病员。大约两星期之后,更为结实、实用的芦席蓬逐步取代了八面透风的帆布帐篷。最初抗震医院没有供电,也没有备用发电机,我们只能用手电筒照明,靠高粱米、压缩饼干充饥,开始了为期一年,终生难忘的非常生活。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直升飞机在天上飞过,或空投救灾物资,或撒下中央、国务院、河北省的慰问信。因为地震灾区邮政瘫痪,医疗队的所有信件都集中起来交给信使,带到唐山,免费寄往各地。佩戴“医疗队”袖章的医务人员,被授权在公路上拦截任何车辆,紧急运送伤员。河北革委会第一书记刘子厚还率领河北省慰问团到医院慰问。颠簸不平的临时公路上则不断有救护车飞驰而来,几乎抬下来的每一个病人都是“急诊”“危重”患者。
当时抗震医院连战备发电机也没有,急诊手术台上就用好几把手电筒代替无影灯进行急诊手术。在短短两个月之内,我见到了几乎全身各部位严重骨折的伤员、截瘫伤员、严重感染的伤员,也见到了平时罕见的急性结核,甚至烈性传染病“炭疽”。因为地震外伤造成不少截瘫病例,许多伤员发生严重的尿潴留,痛苦不堪,而当地的所有医疗部门都无法提供导尿管。医疗队不得不用输血袋上的软滴管代替导尿管,为伤员缓解痛苦。伤员一旦解除了生命危机,就派人送到附近的火车站,转到全国各地的医院继续治疗。
地震灾区的供水系统普遍受到严重破坏,抗震医院没有自来水供应。我们在院里挖了一口临时水井。井里的水煮沸以后用来消毒手术器械,而医护人员自己却没有足够的干净饮用水。临时医院里没有合格的卫生和通风设备,附近又临时掩埋着因重伤死亡的伤员,苍蝇老是飞来飞去。不少医生、护士、医学生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所能吃到的饮食只有压缩饼干、水煮高粱米和缺盐的白菜汤。而一日三餐供应的缺盐白菜汤,被大家戏称为“抗震1号汤”。当时能吃到一顿饺子,那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享受。因为过度疲劳、缺乏睡眠、缺乏营养,不少人先后病倒了。不少人不顾领导的劝阻甚至“警告”,依然坚持在病房里值班。
面对这场前所未见的特大灾难和医院的紧急情况,医疗队领导命我立即搭乘当天去上海的三叉戟飞机,赶回上海。我连夜向医学院领导汇报灾区的情况,然后从医学院的食堂拿来十斤食盐,请附属医院火速送来200根导尿管,第二天一早我又匆匆飞回唐山,立即搭乘一辆运伤员的救护车,奔回抗震医院,解救燃眉之急。就在简陋的抗震棚里,我们不仅收治了大批来自唐山市的危重病人,建立了近乎完备的临床化验室、药房,接生了震后的第一个婴儿。我的专业是病理学。最紧急的二个月过去之后,我拿着抗震医院的介绍信到北京,在协和医院的协助下,购买了一套临床病理科必须的设备器材和试剂,在抗震医院开始了第一例稀有病例的病理尸检和临床病理研讨会(CPC)。那个病例的关键标本,后来被带回上海,收藏在病理学教研室。
我们除了各种常规医疗工作,还收集各病区的动人故事,用钢板、铁笔刻印稿件,编辑出第一期《战地小报》,用滚筒油印机印刷之后发给全院各个病区。我至今还珍藏着一份当时的小报。
大地震之后,唐山依然频频发生余震。大约在8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学从附近的部队赶到抗震医院来看望我们。那天晚上,我们留校的四位老同学特地请厨房的师傅为我们临时加了几个菜,招待这位大难不死的老同学。
饭后我们几个人正在聊天,脚下的大地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地里还发出隆隆的地声,好像有几百辆大卡车从地里滚滚开过。我们立即意识到是一次大地震来临了,立即手拉着手朝门口奔去。奇怪的是,我们的双脚好像被巨大的磁石牢牢吸引住了,无论如何也迈不出一步。只能互相拉着,站在原地,准备着同归于尽。我的心头被一阵难以名状的恐惧感笼罩着。那时候只听到外面破房子“砰砰砰”倒塌的声音和病房里病人惊叫的声音。地震持续了大约十几秒钟才平静下来。事后知道,那是一次7.1级的特大余震。
第二天上午,我们五位震后余生的老同学特地站在医院门口,拍下了一张终生难忘的合影。为了拍好这张照片,我还特地找来一块废木板,拿出我学木工的手艺,给医院制作了一块简易的牌匾,再用黑色油漆工工整整地写上“丰润抗震医院”六个大字,挂在医院的“大门口”。我根本没有料到,那块最初仅仅为了拍照而悬挂的简易牌匾,居然成了人们在废墟之中寻找“抗震医院”的重要地标。
最艰苦的两个月结束后,抗震医院的任务从救治危重病员逐渐变成诊治当地疑难疾病、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的教学医院。医院的胸外科教授已经可以成功地从事心脏外科手术,各临床科室也恢复了相当正规的临床教学和会诊活动。不久,第一批医疗队换班。我则回上海参加抗震救灾报告团,然后作为留守的“老队员”,从上海迎接新一批医护人员前往丰润抗震医院。直到今日,我们这些第一批到达唐山地震灾区的医疗队员之间,不仅互相戏称为“唐山帮”,而且还结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生死患难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