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救援的忧与乐
2016-08-12 作者:刘福官口述者:刘福官
采访者:江云(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
朱文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人力资源部科员)
时间:2016年1月25日
地点: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西院门诊六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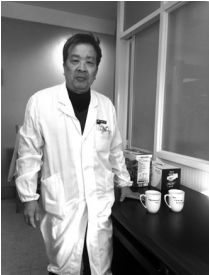
刘福官,1948 年生。1973 年 9 月参加工作。曾担任曙光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1976 年赴唐山参加“唐山大地震”医疗救援工作,为曙光医院第三批赴唐山医疗队队长。
1976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相继有三位伟人去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同样震惊世界的,还有发生在那一年7月28日凌晨的唐山大地震,几乎毁灭了整个唐山市。1976年 9月底,我作为第三批赴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员,带着上海人民的嘱托,告别了同事、亲人和刚刚十个月大的儿子,赴唐山灾区。记得当大客车把我们从唐山林西矿古冶车站接到当时的医疗点—林西矿广场的简易帐篷时,已是下午。简单的交接仪式,还没有听明白该咋办、住什么地方、行李放哪儿,就有人来说:“有病人来看病,哪位医生去……”我们还愣着,以为应该有“值班医生去……”匆忙中,我们便真正开始了抗震救灾的医疗工作。
过“三关”
来到唐山,首先要过地震关。我们每个医疗队员来唐山是抗震救灾,但什么是地震,地震的威力有多大,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来唐山之前仅从书上学过。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位科学家叫张衡,发明了地动仪,据说可预测地震发生的方位,但其真实的意义,只是从书本到书本。来到灾区,我目睹整个唐山市被破坏的景象:道路开裂,桥梁倒塌,房屋毁坏和大量人员的伤亡,方知地震是什么。虽说那时余震经常发生,我们所遇到的真正有破坏力的7级左右的余震有两次:一次是1976年11月初,发生在晚上9时左右,我们正在宿舍中唠家常,突然有人说:“地震了!”我们随即看抗震房梁是不是会塌下来。只见房梁在无规律地扭动,不时发出“吱吱”声。不知什么时候地震停了,有人看表,地震持续四十多秒。这时屋外传来惊吓声,我们出去一看,有几位女士只穿睡衣裤站在屋外寒风中,冻得直哆嗦。那天晚上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半小时以后,医院一下来了四十多位伤员,都是一些吓坏了在慌乱中摔伤的人。第二次在第二年(1977年)的3月。我们当时正在参观现代化采煤作业区,据说是国内最先进的、从国外进口的全自动作业器械。我们正行进在巷道中,只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我们都惊觉地脱口而出“地震了!”但陪同我们的矿领导却轻描淡写地说:“不是的。是煤矿车相撞发出的声音。没事的。”但同时却加快了行进的速度。等我们下午3点回到队部时,值班的同事告知,中午他们在空地上打羽毛球,只觉得地面像波浪一样起伏运动,人都站不住。一想到我们都在矿井下,真不知咋办,会不会有事。看到我们回队,许多人都问一句话:“都回来了?”我们很奇怪。当大家告诉我们中午又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时,想起矿下的那一个巨响,好险!这次到矿下成了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的下矿参观者,毕竟下次地震什么时候再发生尚有许多不可知性。当然我们比起那些采“黑金”的工人不知要安全多少!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都慢慢习惯了大震三六九、小震日日有的日子,也真正了解了地震的真正内涵。
到唐山灾区后的第二关是生活关。灾区断电、断水、通信不畅、交通不便自无话说,到我们第三批医疗队去的时候已有所恢复,不过余震不断,断电、断水等还时有发生。每当断电时,晚上真是漆黑一片,病房中仅靠几只大马灯、手电,还有摇曳的火烛。宿舍中则只有火烛,还需非常小心,不能多点几支。因为一是要防火,据当时通报,兄弟医院一宿舍发生火灾,七间房在八分钟内迅即化为灰烬!二是要节约,因为下次还要用。好在大家在一起,光线不亮,黑暗中闲聊、胡扯亦无妨碍。生活中缺水,牙不能刷,脸不能洗,澡更不用想。幸好大家有准备,一一都熬过来了。不过有一件事却是有口难言。尽管当时的有关领导非常照顾我们医疗队,尽量多给大米,少搭配杂粮,如小米、高粱、玉米等。小米粥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只能喝半碗,因为下半碗中沙石太多直损牙!高粱米很粘,玉米窝窝头很好看,金黄金黄的,但是一旦冷了硬如石块。而整个冬天的菜大部分是咖喱土豆块和大白菜,如和高粱米饭一起吃,日子久了是“易进难出”。久而久之大家对咖喱土豆发生了抵抗,一个冬季下来,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后门”之难,都觉得火辣辣的。到了1977年3月,我们把剩下的大白菜喂猪时,猪都不愿吃,拱几下就走!
第三关是医疗关。虽说离开上海时,大家有准备,条件艰苦,还不是一样开处方拿药治病!但是到了医疗队才知道,除了我们自己带的药品、器械,地方上是几乎什么都没有,因为开栾煤矿总医院在地震中几乎全毁,医疗人员伤亡严重。在自然光下看病、帐篷中做针拔白内障手术、太阳光下拔龋齿,在病房地铺上为病人行气管切开术,在简易手术室中为外伤病员接骨、清创,在手电、马灯照明下完成一例例外科手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在上海时难以想象的困难,努力工作,用我们每一份力量,减轻唐山人民的痛苦。记得有一次抢救一个4月大的患儿,几乎集中了医疗队中的儿科、外科、呼吸科、耳鼻喉科的大夫进行会诊,讨论救治方案。对着患儿,抱着能呼吸,放下即发生呼吸不畅、继而面色青紫的“怪病”,由于患儿母亲不能讲清病史,大家心里急,又无从下手。我跟在李主任身后,听着他对病情的分析,基本确定患儿无先天性疾病的可能后,李主任决给患儿做喉、食管镜检查,以排除最常见的异物梗阻可能。当麻醉喉镜轻抬起环状软骨时,见食管第一狭窄有一淡红色、略硬的物体。李主任用异物钳轻轻取出后一看,原来是一粒硕大的花生米。患儿呼吸顿时通畅。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了。再次询问之下,才知可能是误吃了4岁大的姐姐吃的花生米。看着患儿母亲千恩万谢,大家都有一份战胜困难后的喜悦,疲劳也顿时减轻了许多。在整整九个月的工作中,这样夜以继日工作的日子不知有多少。我们常听到到抗震医院来就诊的灾区人民说的一句话,“你们上海大夫说咋办就咋办”。这是对我们每个医疗队员的莫大信任,也是夜以继日努力工作的最好回报。
向解放军学习,为灾区人民服务
我们第二抗震医院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上海中医学院的三所附属医院和第二军医大学二所附属医院的医疗队组成。在当时的条件下,解放军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刚到唐山,抗震医院正在规划中,我们只能在帐篷中工作,我接待的第一位病员是咽喉疼痛。我习惯地想拿额镜开灯做检查,可要电没电,要灯没灯,正一筹莫展时,长海医院的李兆基主任就娴熟地把病人请到帐篷边缘,用自然光拿额镜进行检查,非常麻利地处理好病员:无声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解放军的作风是看得到、摸得着的,就在身边。我默默地记住了一条宗旨:一定要好好工作,为唐山的重建,为灾区人民的健康作贡献。由于当时生活水平不太高,卫生条件差,来医疗队的患者,患牙龈脓肿、严重龋者不少,但我们队中没有口腔科医生。为了解除他们的痛苦,我和上海的医院联系,请求领导寄有关口腔疾患治疗的专业书刊,一边学习,一边治病。据记录,光拔龋齿就有一千多颗。看到当地儿童患唇裂较多,在李兆基主任的支持下,我开展唇裂矫治修补术,先后为四十多位患儿成功地进行手术。我们手术室的护士小姐开玩笑的称我为“豁嘴刘”。灾区的老年人中,白内障的患者不少,我就当朱炜敏医师的助手进行针拔白内障手术。那时我、朱医师和二军大的二位主任,既要看门诊,又要管二十多张病床,常常是吃了中饭做手术,做好手术看门诊,晚饭之后再要手术,晚上还要看急诊。工作辛苦自然不用说,但苦中也有乐。尤其每当有病人康复出院,说一声谢谢上海大夫时,心中充满了欢乐。
当我们在援建唐山的上海第七建筑公司领导的支持下,到他们的基地洗了来唐山后的第一次澡时,真像是过节一样高兴。而每当有上海家乡来的慰问团来慰问时,大家都欢欣鼓舞,慰问团带来了上海人民的问候、医院领导的关怀、许许多多的生活用品。虽说当时的副食品不充裕,要计划供应,但是亲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多买一点、多寄一点给我们;不过,更多、更主要的是支援灾区人民的医疗用品。
花果山
记得当时的灾区都是震后留下的断墙残垣,因为处在煤矿区,地上到处可以见到碎散的煤块,就是小溪中流淌的溪水也染上了黑色。到了冬季,我们在抗震房中靠简易的“地炉子”烧煤泥取暖,那是用砖垒的,其下向外开有一方口,其后上部约离地面一米高接火墙,然后在屋外有一烟囱管。唐山的冬天要比上海冷很多,记得最冷的一天是零下十九度。冬季每一处屋外均有几个不断冒黑烟的烟囱,走在路上抬头望天空,晴天黑蒙蒙,阴天蒙蒙黑。我们喜欢穿的白衬衫只要穿上不到一小时就“领、袖”全黑。虽说当时事实是这样,但不能随便讲。
最值得我们回忆的是在矿区前面隔马路相望的一处小山坡上,有一片不大的果园,约有十几亩,我们医疗队员喜欢称它为“花果山”。尤在第二年春天来临时,果树萌芽长叶开花,成了我们的休闲乐园。城市中长大的医疗队员,对花果山的果树究竟是什么树,有一种向往和神秘感。大家众说纷纭,尤其是那一群护士小姐,叽叽喳喳,这个说要是桃树,桃花粉红一片,很是美;那个说如果是梨树,梨花一片白,洁白无瑕。大家都盼望着迷底揭开的那一刻。随着春天阳光的不断照耀,果树终于露出了它真实的面貌,是粉红的桃花。点点花蕾逐渐萌发,随之长出几片绿叶,真像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这是唐山人民给我们的奖励!记得当时我们队里的几位年龄较长的医师,他们喜欢早起,常在天刚亮时就三三两两的来到花果山,在树丛中漫步,呼吸真正的新鲜空气。而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匆匆来到时,往往他们刚要离开。不知不觉中,园中始终保持着不多不少的人流。有时我们实在起得太晚,那中午或晚上一定去一次,去花果山游园、赏花,是繁忙工作之余最美好的享受。每天我们碰面或早餐、午餐时,都会问候一声对方:“花果山去过吗?”花果山是一片洁净的果园,是唐山人民重建家园的希望,也是我们医疗队的乐土!
那些“最”
最特别、欢乐的春节。1977年的春节,是在远离家乡的灾区、抗震救灾房内过的。我们医院的战士、同事,聚集在一起,吃着最简单的食品,却都说着欢乐的故事,使人难以忘却的是儿科王志源医生说的“奶奶”叫法。苏州吴语称“好婆”,说话时人略向前倾,轻声细语,最有亲切感;上海浦东本地人则叫“阿奶”,那是短音,干脆,头略向前,表示间接亲热;北方叫“奶奶”是拖着长长的尾音,似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宁波人称呼“阿娘”是头向后,提声而出,那是因为宁波人吃太多咸鱼咸蟹所致。几声奶奶讲得大家欢乐无限,使我们在异乡享受了一顿文化大餐。
最记不起的是休假日。抗震救灾工作,从一下车到住地开始,每一位救灾队员,都牢记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努力工作,从不计较有没有休息,不论昼夜,只要是为唐山灾区的病员、伤员,都无声上岗,细心诊疗。一般情况下,如坚持1—2周,可能大家都能做到,但要持续9月余,270多个日子,我想能忘我地工作,应是难能可贵的,最记不得的就是自己的休息天。
最盼望的事。在灾区工作忙碌,生活艰苦,心里早有准备,虽说当地有关部门对我们医疗队照顾有加,但毕竟物资有限。好在大家的心里是充实的,心情是快乐的。因为我们的背后,有着家乡的亲人支持,组织的关怀。日子久了,大家还是盼着,盼望着组织和家乡亲人慰问团的到来。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带来亲人的问候,同时还将带来可贵的副食品。尽管那时买肉还要肉票,可是即使是一小块肉,二三包卷子面,也是很贵重的物品。
最高兴的事。救灾工作,夜以继日,病人一拨又一拨,虽然辛苦,可高兴的事,还真不少,我们还逐渐学会找乐子,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如讲个笑话,猜个谜语等等。要说最高兴的事,莫过于看好一个伤病员,做好一个手术,病人康复离院,听到他们说一声“谢谢上海大夫”时,心里甜甜的。
最伟大的力量。当我们刚来到灾区,看到处处都是倒塌的厂房、民居和开裂了的公路时,着实感到了地震的破坏力;在接着经受了二次较大余震后,感受更深,地震时地动山摇,人站在地上犹如在船上一般摇晃—但更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党领导下的人的力量,战胜困难,重建家园的力量更强大。当1977年春天来临时,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将迎来一个时代的春天。
唐山大地震过去四十年了,四十年的历史一瞬间。四十年前的抗震救灾工作历历在目,九个月的工作磨练,锻炼了我。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感到有一种力量,一种精神在激励着我们每个参加抗震救灾的医护人员。
九个月后,当我回到上海,回到亲人身边,看到已学会走路、学会说话的儿子时,感慨万端。当我的儿子看到他妈妈指着照片告诉他这是爸爸、而今站在他面前的这个陌生男人时,迟迟不肯开口。足足相视了大约五分钟许,在他妈妈的催促下才小声地叫了声“爸爸”。一声爸爸,叫得我热泪盈眶。
九个月的磨练,收获的精神财富是难以量计的,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受益。